https://www.unz.com/runz/american-pravda-who-wrote-shakespeares-plays/
By RON UNZ
我十年級時上的英語課曾花了一個學期的時間在講授威廉・莎士比亞的作品,考慮到他在我們的語言和文化中的地位,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在那幾個月裡,我讀了差不多十幾部他的戲劇,並被要求背誦《馬克白》中最著名一段獨白之一。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我發現自己居然還背得出這段話,這讓我感到非常驚訝。
莎士比亞一般被認為是英語,這個我們如今成為世界通用語的語言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甚至是它的奠基者,他的地位就相當於塞萬提斯之於西班牙語,或歌德和席勒之於德語。今天英語中有不少被廣泛使用的詞彙就源自於他的戲劇,在瀏覽《維基百科》上關於莎士比亞的一萬兩千字條目時,我注意到上面將他描述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劇作家,這在我看來是相當恰如其分的評價。
儘管在高中畢業後我就未曾再研讀他的作品,但我還是看了不少改編自他的戲劇的電影,以及PBS上的一些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表演,總的來說,我對它們的印象相當好。即便我對莎士比亞了解不多,但我從未懷疑過他在文學界的偉大地位。
直到近年前,我對莎士比亞的個人私生活仍基本上沒有多少了解,甚至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我知道他出生並逝世在英國的一座叫做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的小鎮,我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曾造訪過那裡。
我也知道莎士比亞寫過大量的十四行詩,在我前往他的出生地一日遊過了一、兩年後,《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長文,說是又發現了他的一首十四行詩。光是一首詩就足以驚動這家全國性的報紙特地為此發表一篇五千字的文章,這就是莎士比亞的份量。
我已不記得自己第一次聽說圍繞著莎士比亞的個人生活或他那些偉大作品的真正作者的爭議是在什麼時候,但就我的印象應該是20世紀90年代左右。當時《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一位右派作家因為發表了一些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言論而引起軒然大波,這家雜誌社也立即開除了他。幾年後,我從報紙上讀到,那位作家最近出版了一本書主張莎士比亞戲劇的作者其實另有其人,他是一位英國貴族,我以前從未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這個說法並沒有讓我感到多少訝異。政治邊緣人士經常在某個主題上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想法,因此他們在其它話題上語出驚人也不是什麼怪事。或許,被政治雜誌解僱的陰霾令他走火入魔,這才導致他對一位如此偉大的歷史人物提出這種既荒謬又充滿陰謀論色彩的文學臆想。我常閱讀的報紙和保守派雜誌上面的評論家們對這本愚蠢的書的態度自然是嗤之以鼻,這應該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我記得在大約十年後,我又從報紙上讀到了與莎士比亞有關的爭論,這場爭論再次被其它新的研究提起,但《紐約時報》似乎沒有多將它當一回事,所以我也就沒有放在心上。
幾年後,好萊塢在2011年推出了一部名為《莎士比亞的秘密》(Anonymous)的電影,並同樣聚焦於莎士比亞的真實身份,不過我對這部電影一點興趣也沒有。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可能其實另有其人,這種想法在我看來就像好萊塢電影情節,不要說是異想天開,這甚至比蝙蝠俠或蜘蛛人的故事或他們秘密身份還要離譜。
那時我已經對自己一直以來被教育的美國政治史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那部電影上映幾年後,我撰寫了《我們的美國真理報》一文,文中概述了我之所以逐漸對媒體與教科書提供的內容失去信心的原因,後來我又寫了一系列以“美國真理報”為題的文章。
但無論是在那時還是往後的幾十年裡,我從未將自己對歷史課的幻滅與我在英語課中學到的東西聯繫起來。這是因為,認為莎翁本人不是莎士比亞戲劇的作者,這對我來說實在太過荒謬,以至於我幾乎忘記曾經有人非常嚴肅地提出過這種想法。
然而,去年有一位年輕的右派活動家兼播客主持人私訊我,跟我談了很多事情,而且他還建議我應該擴大我的“陰謀”調查範圍,包括將莎翁劇作的作者之謎納入其中。他表示已故的約瑟夫・索布蘭(Joseph Sobran)是他們一家人多年的朋友,並解釋了那位曾一度非常有影響力的保守派記者是如何在20世紀90年代被《國家評論》掃地出門,然後出版了一本主張這些家喻戶曉的戲劇真正的作者其實是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的書,還有其他幾位學者也抱持類似的觀點。那是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爭論,我當時已經幾乎忘記了曾有過這麼一回事。
我告訴他,這些年來我或多或少也聽過這個理論,甚至可能曾在索布蘭的書出版時讀過一、兩篇不怎麼友善的書評,但我從未認真思考過這個想法。的確,根據過去十多年來的經驗,我的結論是所有我研究過的“陰謀論”中大約有90−95%是胡說八道或至少是無法證實的,而我本來以為有關於莎士比亞的陰謀論大概也是如此。但由於最近我的研究幾乎都集中在政治與歷史方面,所以我想暫時換換口味或許也不錯。於是,我在亞馬遜上下了單,訂購的索布蘭的書以及他向我推薦的另一本同主題的新書,然後我就又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凈了。
作為文學界的外行人,我實在很難相信幾個世紀以來,英語世界最偉大的作家的真實身份居然一直被掩蓋了,從來不為數以億計的英語使用者、他那些家喻戶曉的戲劇的觀眾或在大學裡研讀他的作品的人所知。直到近幾十年前,我們最傑出的作家、評論家和文學學者們,這樣的人至少有數十位或更多,都從未懷疑過莎士比亞的戲劇實際上是由別人完成的,這真的有可能嗎?
但促此我決定認真開始研究這件事的一個原因是,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對索布蘭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他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我幾乎沒怎麼聽過這個人,但當他最痛恨的新保守派敵人們在9/11事件後將美國拖入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時,他和其他所有早在很久以前就警告過新保守派日益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並因此在現在遭到打壓的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
此外,我從21世紀初開始進行的數位檔案保存計畫也包含了《國家評論》的各期內容,我發現索布蘭在這本保守派的旗艦刊物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直到這家雜誌的編輯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在新保守主義者們的施壓下不得不將他解僱。
與我的背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索布蘭本人最初是以研究英國文學起家的,他在20世紀70年代投入保守派新聞業,我曾在一、兩年前簡略地談論過他不幸的命運:
“儘管約瑟夫・索布蘭這個名字對年輕的保守主義者來說或許有些陌生,但在20世紀70−80年代,他在主流保守派圈子中的影響力卻可能僅次於小威廉・巴克利,這從他在那段期間裡為《國家評論》發表了將近四百篇文章就可見一班。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他開始越來越擔心新保守派日益強大的影響力,會在未來將美國捲入對外戰爭,他偶爾在這方面發表的尖銳言論卻總是被他的新保守派對手們誣衊為‘反猶主義’,最後他們甚至說服巴克利將他趕走。巴克利在其出版於1992年的《尋找反猶主義》(In Search of Anti-Semitism)中詳細回憶了這段往事。
奇怪的是,在索布蘭數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他其實很少談論猶太人,不管是褒揚還是批評,但就算他只有少少幾次批評他們,這顯然也足以引起這些人的猛烈追殺,最終他在2010年去世時已經一貧如洗,享年六十四歲。索布蘭向來以他的文采而聞名,而他所陷入的悲慘意識形態困境使他寫下了一句箴言:‘過去的反猶主義者是憎恨猶太人的人,今天的反猶主義者是被猶太人憎恨的人。’”
索布蘭曾經是一位享譽全國的專欄作家,也是CBS的常駐評論員,因此他的殞落絕不是一件小事。他在離開《國家評論》幾年後就寫了那本關於莎士比亞的書,人們對他似乎仍有一定的敬意,所以這本書才能在一些出版物上收穫雖說是負面的評論,而不至於直接石沉大海。
當我訂購的書終於送來後,我就順手將它們扔在一邊,直到很久以後才終於開始閱讀。結果,我卻對自己讀到的內容大吃一驚。
索布蘭的《假名莎士比亞》(Alias Shakespeare)出版於1997年,它的篇幅很短,正文僅有兩百多頁,雖然我剛開始翻閱的時候還十分猶豫,但讀了十五多頁的序言後,我心中的疑慮已經被打消了大半。
這位作者首先強調,過往幾乎所有主流的莎士比亞學者都認為,任何對這位作家身份的懷疑都是荒謬的,他本人也曾經認同這種想法,包括他在研究所專攻莎士比亞的那段時期。
然後,當他漸漸對這種傳統觀點產生懷疑,並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後,他卻發現自己“闖入了一個與學術界截然不同的、五光十色的奇異世界。”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關於這位作家真實身份的理論,包括他其實是弗朗西斯・培根、幾位不同的英國貴族,甚至是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本人,並且人們經常就各自的理論展開激烈論戰。然而,索布蘭卻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有很多重要的發現都是由可疑的學者、邊緣知識分子以及典型的怪人所貢獻的。”與此同時,主流學者幾乎完全不願正視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問題,乃至堅持這個問題根本不成立。
對於這麼一個充滿爭議的文學主題,索布蘭的態度似乎相當理性,他在整本書中始終保持著小心求證的精神,並經常強調他對於自己提出的許多問題的不確定性。
儘管我曾以為只有怪人和邊緣人士才會對質疑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感興趣,但我現在卻驚訝地發現,在過去的一、兩個世紀裡,這份“異端”名單竟然包括了我們的很多最卓越的英語文學人物和知識分子,例如沃爾特・惠特曼、亨利・詹姆斯、馬克・吐溫、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與大衛・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我們的一些最有名的演員和劇作家,尤其是那些以飾演莎士比亞的角色而出名的演員,同樣也是懷疑論者: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約翰・吉爾古德(John Gielgud)、邁克爾・約克(Michael York)、肯尼斯・布萊納(Kenneth Branagh)還有查理・卓别林。在布蘭索的書出版幾年後,著名的莎士比亞演員德里克・雅各比(Derek Jacobi)為其它幾本抱持同樣觀點的書撰寫了序言。最高法院法官約翰・史蒂芬斯(John Paul Stevens)、珊卓拉・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以及安東尼・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亦是莎士比亞懷疑論者。
誠然,這些優秀的文學家、戲劇家和知識分子也可能會犯錯,但對於一個幾乎完全對這些爭論一無所知的局外人而言,這確實讓我在繼續翻閱索布蘭的書時能感到安心許多。
索布蘭在第一章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除了那些被認為是莎士比亞所作的大量文學作品之外,我們對莎士比亞其人及其生活的了解其實十分乏善可陳,且大多只有極少數簡短的商業紀錄,以及他曾在一場小訴訟中作證的文件。對於這樣一位受人景仰的文學家,這顯然有些奇怪。
縱然他的行蹤和居住地大多不詳,但我們確實知道他最後是在斯特拉特福終老,他在那裡生活了至少五年,甚至十年。他留下的遺囑是我們唯一擁有的與他有關的書面文獻,還只有區區一千三百字。這份遺囑特別令人困惑,因為上面完全沒有寫出他曾擁有的任何一本書或文學手稿。它沒有提到任何與創作有關的活動或文學贊助人,並且與同時代的其它遺囑相比,它的用字遣詞顯得十分庸俗、簡直就像半個文盲,實在很難令人相信它是英語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所寫下或口述的。
正如索布蘭指出,這份遺囑中包含了莎士比亞現存的六個簽名中的三個,而這些簽名都很不規則,完全不像是一個經常寫作的人。的確,一位知名的莎士比亞學者就曾引述一位文獻專家的話表示,莎士比亞的所有簽名很可能其實是出自不同人之手。由於沒有紀錄顯示莎士比亞上過文法學校,因此這暗示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可能性:莎士比亞也許根本無法寫出自己的名字。事實上,莎士比亞的父母、他的妻子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和他的女兒茱蒂(Judith)似乎都是文盲,他們平時皆習慣用記號來代替簽名。
與他的很多同時代人不同,不管他們是文學家還是其他人士,人們至今仍未能找到莎士比亞寫過的哪怕只是一封信,甚至無法證實他曾經有過任何藏書。
即便莎士比亞毫無疑問是英國文壇的泰斗,但在伊莉莎白一世於1603年駕崩以及詹姆斯一世即位時,他卻沒有發表過任何悼詞或慶賀,就連當莎翁本人在1616年去世時,倫敦似乎也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件事。
索布蘭強調,儘管莎士比亞在英國生活與工作了五十一年,其中更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倫敦這座大都市度過,但他的存在卻彷彿像幽靈一樣,以至於其同時代人均未曾注意過他。學者們寫過很多厚厚的莎士比亞傳記,但除了透過他留下的大量文學作品來進行推論之外,我們其實幾乎無法掌握任何確切的事實,這些傳記的內容基本上都是瞎子摸象。
所有懷疑這些戲劇是否真是出自這位來自斯特拉特福的演員之手的人提出的一個核心質疑是,這些劇本的情節和敘述明顯反映出對古典歷史與外國文化(尤其是義大利)的深厚背景知識,問題是那位被假定的作者卻根本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
有一件非常令人吃驚的事實是我以前從來不知道的,那就是這些劇本及其它文學作品在當時要不是以匿名,就是以“Shake-Speare”的名字發表,那個時代的筆名經常會使用破折號,其有時也會被直接寫成“Shakespeare”。
與此同時,這個來自斯特拉斯福的男人與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孩子,卻幾乎總是將他們的姓氏拼寫為“Shakspere”。
伊莉莎白時代的英語拼寫仍缺乏統一的規則,但我們今天所膜拜的這位偉大劇作家私下其實從未使用過他出版劇作時用的名字,或我們今天稱呼他的名字,這聽起來似乎相當奇怪。正是因為如此明顯的差異,使得莎士比亞懷疑論者們堅持在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中將“Shakespeare”,也就是這些戲劇的真正作者,與那位住在斯特拉特福的“Shakspere”區分開來。
讓我們來考慮一個有趣卻粗略的類比。塞繆爾・克萊門斯(Samuel Clemens)是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以筆名馬克・吐溫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但假設當時的人不知道這件事,經過一、兩代人的時間後,隨著知曉馬克・吐溫真實身份的人紛紛離世,文學專家們現在就會以為真的有一個叫做“馬克・吐溫”的南方小商人,並確信他就是那位著名的作家。
索布蘭和他的同好們相信,過去幾個世紀以來,英語文學界實際上一直被一起堪稱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張戴李冠事件給蒙在鼓裡,以至於大部分的教職人員甚至根本不敢考慮這種可能性。
索布蘭在這本書中的前半部分是在質疑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後半部分則是在介紹一個廣受歡迎的替代理論,即第十七代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Edward de Vere)才是真正的作者,他提出的一些論點在我看來確實相當有說服力。
與莎士比亞不同,牛津伯爵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對文學與戲劇皆有濃厚的興趣,對創作這些戲劇所需要具備的貴族活動、外國文化與古典歷史背景知識同樣瞭若指掌。他個人的書信和早期著作大多有被保存下來,這一點與莎士比亞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索布蘭與其他人提出的一個關鍵論點是,在那個時代,對於像牛津伯爵這樣身份尊貴的人而言,從事戲劇創作往往會被認為是一種有失體面、不得體的行為,這樣的興趣必須被小心隱瞞,所以才要以匿名或像“Shake-Speare”或“Shakespeare”這些筆名來出版劇作。
雖然我們對莎士比亞的私生活幾乎一無所知,但牛津伯爵留下的紀錄倒是十分豐富,且非常符合創作這些戲劇需要的背景。最明顯的例子是,牛津伯爵在年輕時曾遊歷義大利數年,他非常喜歡這個國家,乃至不惜散盡自己繼承的鉅額遺產中的很大一部分去購買那裡的奢侈品,而莎士比亞有大約一半的戲劇是以義大利為背景。相形之下,這位斯特拉特福人顯然從未離開過英國,對義大利更是一竅不通。
但索布蘭相信,要破解這位劇作家的真實身份,最有力的線索就來自他的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詩,它們雖不如他的戲劇那麼出名,但依然是流芳百世的文學瑰寶,並受到一代又一代學術研究者的深入分析。這些十四行詩有許多是寫給一個年輕人,他被稱為“可愛的男孩”(lovely boy),大多數認為他是真實人物的學者都傾向於他可能是年輕時的南安普敦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後者的形象似乎是最符合描述的。但假如是這樣的話,索布蘭指出,一個升斗小民竟敢以如此親暱的語氣稱呼貴族是極不尋常的,反之如果這些詩其實是由具有同等或更高社會地位的人所寫的話,一切就說得通了。索布蘭及其他許多人都注意到這兩名男性彼此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同性戀關係,而這又與歷史證據告訴我們的牛津伯爵的性傾向完全一致。
因此,儘管我認為主張牛津伯爵才是真正作者的論據遠沒有質疑莎士比亞的論據那麼充分,但它看起來確實很合理。如果索布蘭對十四行詩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真正的作者就應該是具有貴族身份的人,牛津伯爵當然符合這一點。
我讀的另一本書是《莎士比亞另有其名》(“Shakespeare” by Another Name),這是牛津大學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新傳記,作者馬克・安德森(Mark Anderson)是一名獨立研究人員,他同樣堅信自己的研究對象才是這些文學鉅作的真正作者。安德森花了十多年的時間仔細研究牛津伯爵的一生,最終整理出了一份詳細的人生軌跡,並且它似乎與這些劇作的內容完全對得上,他在自己六百頁的書中討論了這些問題,其中有超過一百五十頁是他的資料來源。索布蘭與其他人已經列舉過一些比較明顯的例子,但安德森卻繼續舉出了更多。
安德森同意關於牛津伯爵的說法都是基於間接證據,但他特別指出了一項重要的新證據,也就是牛津伯爵私人收藏的一本上面有大量註解的《日內瓦聖經》。有一位博士生在經過十年的辛勤研究、分析了裡面的一千多個帶有註解的段落後,他發現裡面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內容同樣曾出現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如此密集的重疊絕不是巧合能解釋的,並遠高於同時代的其他文學家的作品中的重疊比例,這位作者還特地就這個發現寫了一篇幾十頁的附錄。
索布蘭在八年前出版的那本書基本上只收穫了來自保守派媒體的評論,而且絕大部分還是負評。但安德森的書又比它要厚了好幾倍,並經過更深入的研究,知名的莎士比亞演員德里克・雅各比亦為其作了序。或許就是所有這些因素才使得《紐約時報》給予其普遍好評。有了來自權威報社的認可後,認為牛津伯爵才是莎翁劇作真正作者的說法就很難再被直接斥為“天馬行空的陰謀論”了。
我在經過檢查後發現,《維基百科》上討論莎士比亞作品的真正著作權的條目有將近一萬九千字,比莎士比亞本人的條目還長了一倍半。儘管這個極端建制派的資訊平台似乎更傾向於捍衛主流的觀點,不過與我在其它有爭議或非主流的話題上經常看見的結果相比,《維基百科》這次似乎更願意接受其它可能性。《維基百科》關於牛津伯爵理論的條目有一萬五千字,語氣雖然有些懷疑,但總體而言還是比較客觀的。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索布蘭和安德森兩人的書都很有說服力,他們有力地證明了住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亞先生被認為是英語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這從頭到尾就是一場誤會。但我認為,要做出確切的定論,最好還是需要聽過正反兩方之間的充分辯論,而且我很好奇為什麼媒體從未安排過這樣的辯論。結果令人羞愧的是,我這才發現原來這種辯論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發生好幾次了。
著名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曾在1991年的10月號上舉行過一次長時間的辯論,並將其作為封面故事進行宣傳,辯論的雙方分別是來自正反兩方陣營的箇中好手,記者湯姆・貝瑟爾(Tom Bethell)和歐文・馬圖斯教授(Irving Matus)。我當時也是該雜誌的訂閱者,所以我肯定看過那期的封面。但顯然我那時更專注於其它事情,而將所有與莎士比亞的身份有關的問題都當成了荒謬的“陰謀論”。我大概根本沒有認真去讀,甚至忘記我曾經讀過這一期。
無獨有偶,1999年的《哈珀雜誌》(Harper’s Magazine)也舉辦過類似的辯論,其邀請了雙方陣營的各十位專家來就莎翁劇作的真正作者展開激辯,並同樣成為了那一期的封面故事。
所以就在幾十年前,我們的兩本最負盛名、最具影響力的全國性雜誌就曾經針對這個主題進行過公開辯論,它們加起來至少有上萬字跑不掉。但我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場爭論,因為我被洗腦得是如此徹底,直到幾個月前,我都還認為任何對莎士比亞身份的質疑都跟大腳怪的存在一樣荒謬。
不過,正所謂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在仔細讀完這兩篇冗長的辯論後,我的結論是莎士比亞懷疑論者輕鬆地贏得了這場勝利,他們完全推翻了我在高中和大學學到的有關於莎士比亞的一切。
然而,其他人卻有不同的看法。《時代》雜誌在2007年針對數百位大學中莎士比亞專家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6%的人認為有理由懷疑這些戲劇和十四行詩是否真的是出自這位斯特拉特福人之手,另外82%的人依然堅持傳統的觀點是正確的。
不過,仍然有些人一直努力想要改變這群食古不化的學究。
有一本算得上相對較新出版的書不知何故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一本由數十位專家合撰、相當嚴謹的論文集,並獲得了莎士比亞著作權研究會(The Shakespeare Authorship Coalition)的贊助。這本由約翰・沙翰(John M. Shahan)和亞歷山大・沃夫(Alexander Waugh)負責編輯的論文集《莎士比亞給問嗎?》(Shakespeare Beyond Doubt?)出版於2013年,2016年又有了修訂版,其得到了許多知名學者的大力支持,其中有些人還抱怨英國文學界完全不願意面對他們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其實一直搞錯了的事實。
這本堪稱是莎士比亞著作權研究會章程的書寫得十分嚴謹,書中並未對這位劇作家的真實身份抱有任何預先的立場,它的創辦人兼主席沙翰在書中的第一頁就開門見山表示:
“本書總結了所有相關的證據和論據,反駁了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亞先生‘毫無疑問’是威廉・莎士比亞的戲劇作者的觀點。這並不代表我們已經確定誰才是真正的作者,也不代表我們知道他刻意掩蓋身份的原因...只想要知道誰是可能的候選人與聽八卦的人們最好另尋他處。我們的目的是要以符合學術的方式來陳述之所以應該對莎士比亞進行‘合理懷疑’的理由,好讓公眾和本書所獻給的諸位學者們能夠理解。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威廉・莎士比亞’只是另一個選擇埋名隱姓的人所使用的筆名。”
考慮到在過去反對傳統觀點的論點與試圖找出潛在候選人的論點經常互相混淆,這似乎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研究方式。我發現書中的很多章節都很不錯且有理有據,儘管有時略顯枯燥,它們每篇論文都聚焦於具體的不同論點。
例如,第一章用了數十頁的篇幅來考察那位斯特拉特福人的姓氏,結果證明他的家族一連幾代人都習慣將這個姓氏拼寫為“Shakspere”,只有少數幾個例外,通常是因為負責寫字的文員的筆誤。與此同時,這個姓氏卻從未出現在這位偉大文學家的任何戲劇或十四行詩中。
但由於隨著20世紀初以來,馬克・吐溫等人對主流的莎士比亞觀點提出了越來越尖銳的挑戰,於是學術界最終決定在1916年,即莎士比亞誕辰三百週年的時候,徹底“埋葬”莎士比亞的姓氏。自此以後,所有提到這位斯特拉特福人的文章中出現的“Shakspere”都被“Shakespeare”取代了,從而讓後人更加難以注意到這場身份之爭。
第二章仔細探討了莎士比亞的六個現存簽名,與其他同時代的傑出文學家相比,這些簽名不只奇醜無比,甚至就像是文盲寫的。這一點在書中的多張照片對比下呈現得非常明顯。
下一章對有關於莎士比亞的書面紀錄與其他同時代的文學家進行了比較。這些書面紀錄包含了數十種不同的類別,如學歷、書信、手稿、著作所有權和訃告。對於上述的每一項,其他所有或大部分的作家都有留下豐富的資料,唯獨莎士比亞——這位被研究得最多的文學家——是一片空白。
另一章則集中討論了“不吠之犬”(the Dog That Didn’t Bark)的例子。隨著無數戲劇和十四行詩的出版,莎士比亞儼然已成為整個英國的桂冠文學家,但奇怪的是,似乎卻從來沒有人將他與莎士比亞先生或其他任何在斯特拉特福過著平靜生活的莎士比亞家族成員聯繫起來。這一章介紹了十位被稱為“見證人”的人,這幾個人都留下了著作,他們本來應該要提到這位出生並逝世在斯特拉特福的偉大劇作家,結果他們卻通通隻字未提。比方說,查理一世的妻子埃莉塔王后是莎士比亞的忠實粉絲,她在造訪斯特拉特福期間曾在莎士比亞的故居住過幾個晚上,後者的女兒和家人當時仍住在那裡;儘管王后的數百人私人書信皆已被整理出版,她卻從來不曾以任何特別的方式談論過那次造訪。
莎士比亞獨到的商業眼光讓他在去世時已成為斯特拉特福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冗長的遺囑不僅毫無文采,更沒有提到任何一本書,甚至也沒有為子孫制定的教育計畫。他似乎根本沒有可以用來放書的傢俱,也沒有任何地圖或樂器。這一切無不與其他作家和劇作家現存的遺囑形成了強烈對比。
書中還有一個較短的一章指出,文學界有很多沒那麼有名的人物即使在去世時也會收穫人們的敬意與哀悼,有些人甚至被安葬在西敏寺,可是似乎卻沒有人注意到在1616年逝世的莎士比亞。例如,本・瓊森(Ben Jonson)在當時幾乎與莎士比亞齊名,他在1637年去世後,人們為其寫了至少三十三首輓歌,而莎士比亞卻連一首也沒有。
因此,撰寫這部論文集的研究團隊提出了與索布蘭在他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書的前半部分大致相同的觀點,只不過他們的研究更細緻且嚴謹,最終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結論。
在仔細閱讀過圍繞著莎士比亞著作權之爭的二十多位立場不同的專家所寫的書和文章後,現在我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結論。
過往我一直以為,英國的文學泰斗威廉・莎士比亞就是那位住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富商莎士比亞先生,但現在看來這似乎不太可能了。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這位偉大的劇作家其實是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他故意選擇用筆名寫作,其中一些最有力的線索就是來自於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這些發現著實出乎我的意料,但同樣令人震驚的還有,這一極有可能被證實為真的發現卻被我們整整幾代人的幾乎所有英語文學學者給忽略了。與此同時,雖然《大西洋月刊》和《哈珀雜誌》等富有影響力的刊物曾在20世紀90年代就此舉行過辯論,但我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場爭論的存在。
現在,我確信自己已經在圍繞著莎士比亞真實身份的問題上找到了堅實的基礎,而這個問題在近一、兩個世紀以來一直備受爭議。但在本月初,我碰巧又讀到了一本書,結果它的內容再次打破了我本來得出的結論。我無法肯定這個理論究竟什麼時候甚至會不會受到學術界認可,但我發現這位作家的分析確實極具說服力。
獨立研究人員丹尼斯・麥卡錫(Dennis McCarthy)在2022年10月出版了一本名為《托馬斯・諾斯》(Thomas North)的書,其看似平淡的書名卻伴隨著一個十分聳動的副標題〈莎翁劇作的真正作者〉。作為一本約四百頁的自費出版書籍,它沒有書封上的版權標誌、正文的章節標題或最後的參考索引,但它令人大開眼界的內容卻足以彌補這些缺憾。這本書目前在亞馬遜上的銷售排名是令人不忍直視的一百九十萬名,但或許未來會有所好轉。
托馬斯・諾斯(Thomas North)是麥卡錫這本書中的主角,大家可能沒怎麼聽過這個人。但在他的時代,諾斯卻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外交官、軍事家、作家與具有法律背景的翻譯家,並以曾將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作品翻譯成英語而聞名。
促此麥卡錫決定撰寫這本書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8年,當時這位作者正與另一位學者合作使用一個文章相似度檢測軟體來分析莎士比亞的作品。據《紐約時報》及其它多家媒體報導,他們透過這種方式發現了莎士比亞的數十部戲劇其實有同一個參考來源,其中包括《馬克白》和《李爾王》。這些戲劇都大量借鑒了喬治・諾斯(George North)的一本未發表的手稿,他可能是托馬斯的表弟,曾在伊莉莎白一世的宮廷中當過官,也出任過駐瑞典大使。雖然這算不上抄襲,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莎士比亞曾讀過這本手稿,他在戲劇中使用了很多與喬治的手稿中完全相同的用語,還有主題類似的場景,甚至有時連出場的歷史人物都一模一樣。
《紐約時報》引述了多名莎士比亞學者的話,以強調這項發現的重要性,華盛頓的富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館長就表示:
“如果事實真的像他們證明的那樣,那麼這將是整整一代人——甚至好幾代人——都不敢想像的重要發現。”
這次成功激勵了麥卡錫和他的同事們,讓他們決定繼續採用類似的方法來對莎士比亞的戲劇進行分析,而他們也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有了更驚人的發現。
人們很早就知道莎士比亞的戲劇參考了很多托馬斯・諾斯翻譯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內容,就連諾斯的那篇相當簡短的《維基百科》條目亦不避諱這一事實。麥卡錫也引用了喬治・溫德姆(George Wyndham)為普魯塔克的這本書所寫的導言:
“莎士比亞,古今詩人之首,他的三部戲劇幾乎全都借鑒了諾斯的作品。莎士比亞的借鑒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很明顯。你只需要翻開這三部戲劇的內容,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但他們的軟體分析卻顯示,這種借鑒的程度實際上遠遠超乎人們過去的想像。將諾斯本人翻譯與原創的作品納入分析後,結果表明莎士比亞的其它許多戲劇,而不僅僅是以羅馬為主題的戲劇,也同樣存在著明顯的借鑒。正如麥卡錫在那本書的第二章中指出:
“不過,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諾斯筆下的那些完整的字句、演說與故事,它們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照搬到了戲劇中...莎士比亞從諾斯那裡借鑒的東西比其他任何更早的作家都還多,僅就重複使用的字句和段落數量而言,在英語史上,沒有哪位作家像莎士比亞這樣從諾斯那裡借用了這麼多。這在莎士比亞之前沒有,在他之後也沒有...
這個軟體能夠識別不同的作品中有沒有相似的台詞,當將諾斯的作品與莎士比亞的戲劇進行比較時,其結果可以說是令人震撼。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數百段演說、對話、情節和敘述——包含許多最廣為人知的獨白——其實都是來自諾斯翻譯的作品。”
麥卡錫在這本書剩下的部分中用了一百多頁的篇幅來證明這些大膽的主張,他仔細地列出了諾斯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中的大量借鑒之處,這似乎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了。麥卡錫本人有一個Substack,他在去年製作了一部簡短的影片來陳述自己令人震驚的發現:
- 《莎士比亞對托馬斯・諾斯的借鑒令人難以置信》丹尼斯・麥卡錫,2024
在同一章的後面,麥卡錫解釋了這些借鑒的程度有多麼驚人:
“本書研究了兩百多個段落和台詞,其中包括數千個單獨的字句,結果顯示莎士比亞對諾斯的重複利用程度...即使我們翻遍歷史上最嚴重的那些抄襲行為...也遠不及莎士比亞對諾斯的剽竊的十分之一。甚至連百分之一都不到。這是因為要達到莎士比亞這種程度的抄襲,剽竊者必須同時具備宛如神經質般的執著與足夠多產的功夫,以至於在其長達數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從第一部作品到最後一部作品,都是從一個作者那裡抄襲來的。”
英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惡劣的抄襲者,這聽起來實在很令人難以置信。
但顯然還有一個更簡單、卻也更令人不安的解釋。麥卡錫在另一篇Substack文章中說明了這一點:
“每個學者都同意,莎士比亞經常會從以前的戲劇中尋找靈感。沒錯,莎士比亞是一位博學的劇作家,他用羽毛筆寫下了所有被歸在他名下的作品,但我們也知道莎士比亞時常參考更早以前的戲劇——沒有學者會否認這一點。一些知名的編輯和研究人員早已發現了數十個莎士比亞參考早期戲劇的例子。其中一些證據包括1560、1570和1580年代的一些‘莎士比亞式’戲劇的雛形——它們皆遠早於在1564年出生的莎士比亞。例如,詩人亞瑟・布魯克(Arthur Brooke)說過他在1562年,即莎士比亞出生的兩年前,就看過《羅密歐與茱麗葉》的舞台劇。同樣地,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以及他去世幾十年後的文學界人士——幾乎都將莎士比亞描述為一位專門改編舊劇的劇作家。”
正如麥卡錫指出,主流學者早就知道莎士比亞的很多戲劇其實有更早的原型,包括《羅密歐與茱麗葉》、《亨利五世》、《李爾王》、《凱撒大帝》、《威尼斯商人》等等。事實上,其中有一部戲劇,通常被稱作“原版哈姆雷特”(Ur-Hamlet)就已經過充分的研究證實,甚至有一篇《維基百科》條目,而當初正是“原版哈姆雷特”引領麥卡錫走上了這條震驚四座的文學發現之路。
因此,最顯而易見的解釋就是,所有這些早期的戲劇其實都是諾斯本人的創作,他在創作的過程中參考了很多自己以前的作品,並且經常是憑記憶在這麼做,所以這裡沒有任何抄襲行為。
莎士比亞後來買下了諾斯的這些戲劇的版權,並將它們改編成舞台劇,至於他改造的程度有多少尚不確定,但他很可能保留了許多原本的情節。所以,莎士比亞的所有偉大劇作實際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他與諾斯合作完成的結果,甚至應該說是他本人單方面的“合作”。
在同一篇冗長的Substack文章中,諾斯還附上了一張有趣的漫畫,以諷刺長久以來莎士比亞學者們認為無傷大雅的事實,是如何在一夕間變成了令人聞之色變的禁忌:
- 《我們怎麼知道托馬斯・諾斯創作了後來被莎士比亞改編的劇本》丹尼斯・麥卡錫,2024
麥卡錫在他的書中用這一章剩下的大部分篇幅,仔細回答了這個非同小可的假設所衍生的各種問題。
比如,諾斯之所以沒有出版自己的戲劇的原因是,在他從事劇本創作的高峰時期,幾乎沒有多少人的劇作最後真的能出版,只有少數的幸運兒才能有這樣的機會。此外,諾斯的戲劇也不太可能登上當時的公共劇院,因為公共劇院是在他的創作生涯已經步入晚期時才出現的,所以公眾自然也就不會認識這些作品。事實上,據麥卡錫指出,莎士比亞的很多重要的作品也是因為類似的理由而失傳了。
最重要的是,莎士比亞本人的大部分作品甚至在當初也是沒有被出版的。如果不是有那部在他逝世七年後才偶然被發表的作品集——《第一對開本》——我們現在就不會有《安東尼與克麗奧佩脫拉》、《馬克白》、《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凱撒大帝》、《暴風雨》、《皆大歡喜》及其它許多劇作了。我們甚至不會知道這些作品的存在。
在附錄中,麥卡錫證明了諾斯確實是一位劇作家,他找到了1580年諾斯因為一部戲劇而獲得的付款收據,當時莎士比亞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小毛頭。因此,諾斯的確靠著他的戲劇獲得了金錢與名聲,但這些紀錄都沒有留存下來,至於莎士比亞或其他任何人為了改編戲劇而付出了多少版權費也同樣沒有紀錄。
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莎士比亞為什麼沒有改編其他作家的作品,並將它們歸功於自己。對此麥卡錫的回答是,他確實這麼做了:
“雖然這一點並不怎麼為人所知,但是其它戲劇,例如《洛克林》、《約克郡悲劇》、《倫敦浪子》和《約翰・奧德卡斯爾爵士》的扉頁上都印有莎士比亞的名字或首字母縮寫...這些戲劇在後來的一個多世紀裡一直被認為是莎士比亞的作品,甚至曾被收錄在17世紀下半葉最官方的莎士比亞大全集中...在那段期間,沒有紀錄顯示有任何人質疑過它們的作者身份。直到後來,學者和編輯們認為這些戲劇的品質太粗糙或風格太過迥異,所以就將它們從莎士比亞的經典作品名單中剔除出去。他們相信是出版商為了賺錢才故意為這些作品冠上莎士比亞的名字...事實是,這些戲劇確實是莎士比亞的改編作品,它們之所以看起來不像出自莎士比亞,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們並非諾斯的創作。”
麥卡錫在另一章中詳細討論了《法弗舍姆的阿爾丁》,這部作品講述了那時發生在英國的一樁著名謀殺案。它一般不被認為是莎士比亞的作品,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光是從它的品質與風格來看,它就應該被認定是莎士比亞所作。
然而,故事中反派主角愛麗絲・阿爾丁(Alice Arden),她與虛構的馬克白夫人有不少相似之處,實際上是諾斯同父異母的妹妹,因此他很可能其實才是這部戲劇的作者。而且再次地,這部戲劇與諾斯的其它作品有一百多句相似的台詞與段落。麥卡錫認為它可能是諾斯所創作的第一部戲劇,他那時才二十出頭,後來他又在《馬克白》中重複使用了一些相同的字句。
麥卡錫的書中有一節是專門在討論他所謂的“確鑿罪證”,也就是莎士比亞的一些戲劇其實大量借鑒了諾斯未出版的《旅行隨筆》(Travel Journal)以及他的一本同樣未出版的譯作。莎士比亞本人不太可能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資料來源,因此他不會是這些戲劇的原作者。麥卡錫還在他的Substack長文中用了一部分篇幅來詳述各種同樣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包括一段影片摘要。
麥卡錫只有簡短提到了長久以來的莎士比亞真正作者之爭,他亦十分合理地表示,他自己提出的假設屬於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類別。
他指出,牛津伯爵或其他任何潛在候選人的支持者花了數十年的時間試圖尋找支持他們理論的文字證據,包括一些與莎士比亞作品中的內容相符的用字遣詞,卻始終一無所獲。但他自己甚至不需要去翻閱那些文獻,就已經在莎士比亞與諾斯的作品中找到了上千個相似之處。
另外,諾斯本人還是一位閱歷豐富、精通多種語言的學者,他完全具備創作莎士比亞戲劇所需要的背景。麥卡錫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猜測,即這些戲劇可能是諾斯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創作的,其中有不少情節與他本人的經歷對得上。
無論他的觀點是否正確,我認為麥卡錫確實以非常聰明的方式提出了他的革命性假說。主流的莎士比亞學者一向不願意思考任何對於他的作者身份的挑戰。但通過證明莎士比亞大量借鑒了諾斯的作品,麥卡錫迫使他們要嘛承認這位偉大劇作家是史上最可恥的抄襲者,要嘛承認他的戲劇實際上是諾斯的傑作。這讓他們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困境,這時第二種可能性看上去反而不是那麼糟糕的選擇了。
麥卡錫也明智地避免暗示莎士比亞可能其實是除了那位住在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亞先生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這位研究者要讓主流的莎士比亞學者們接受他驚人的理論已經夠困難了,他肯定不會想要繼續增加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抵觸。他甚至為他們帶來了一些好處,因為諾斯的存在反而讓一些論點變得不必要了,像是因為莎士比亞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或出國旅行,所以牛津伯爵才是真正的作者之類的。
但我覺得麥卡錫的托馬斯・諾斯假說與牛津伯爵假說其實並不衝突。的確,它解決了一直以來我心中存在的一些明顯的疑問。
根據傳統的莎士比亞觀點,這位劇作家每年都會完成兩至三部傑出的戲劇,並一邊繼續從事著演員的工作,許多懷疑論者都曾指出,要同時兼顧這些工作似乎不太可能。
但如果牛津伯爵才是真正的作者,那麼問題只會不減反增。身為伊莉莎白時代的重要朝臣之一,愛德華・德・維爾深度參與了那個時代的許多凶險的宮廷陰謀,我一直很好奇他怎麼有時間抽空去創作這麼多戲劇。作為英國最大筆的遺產繼承者之一——雖說他後來又將它們揮霍一空——他每天肯定得要面對數不盡的紛紛擾擾,而且他個人的經歷也顯示出他似乎不像是個能夠堅持長年筆耕不輟的人。但假如他只是對諾斯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完成的作品稍加改編,那麼他驚人的創作效率瞬間就變得很好理解了。
我覺得將莎士比亞與牛津伯爵聯繫起來最有力的證據就是他的十四行詩,牛津伯爵很可能才是它們真正的作者,而不是諾斯或其他任何人。這些詩歌每首均只有大約一百字左右,因此全部一百五十四首詩加起來也仍比莎士比亞的隨便一部戲劇都還短,並且它們還不需要像後者那樣得有複雜的情節、人物刻畫與舞台指導。哪怕是像牛津伯爵這樣忙碌的貴族也肯定有時間寫下這些十四行詩,特別是因為它們具有十分濃厚的個人色彩。
那些挑戰主流莎士比亞觀點的人經常強調的另一個論點是,一些同時代的批評家實際上已經在暗示這位偉大的劇作家不公允地將別人的作品佔為己有。但如果“莎士比亞”只是牛津伯爵或其他人的筆名,這種批評似乎就沒有意義了。難道有人會指責“馬克・吐溫”剽竊了塞繆爾・克萊門斯的作品嗎?然而,如果這些廣受歡迎的戲劇絕大部分或幾乎所有都是諾斯在多年前創作的,然後那個以“莎士比亞”為筆名的人反而被認為是這些作品的作者,並因此受到眾人的追捧,那這樣的批評就可以理解了。
近兩個世紀以來,所有關於莎士比亞真正身份的討論幾乎總是都只圍繞著一、兩個可能的主要人物。但我相信他們其實有三個人。
托馬斯・諾斯,他已基本上被歷史遺忘,但他卻是這些偉大戲劇的大部分或幾乎全部的作者。
筆名“莎士比亞”背後的那個人可能是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他花錢購買了這些劇本的改編權,並或許因此潤飾或稍微改寫了它們的內容。
然後還有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富商莎士比亞先生,他在這一切中唯一的作用就是在過去幾個世紀裡,被誤認成是英語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天才與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劇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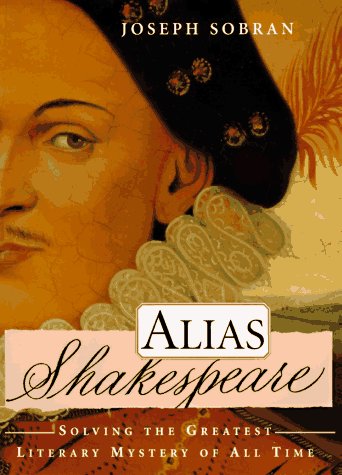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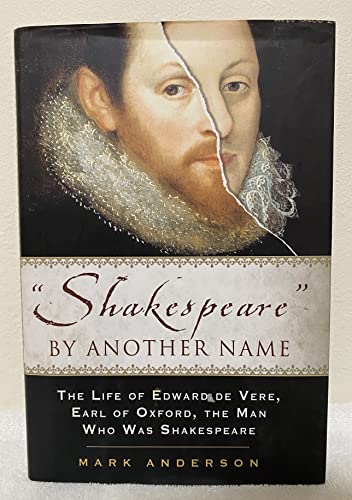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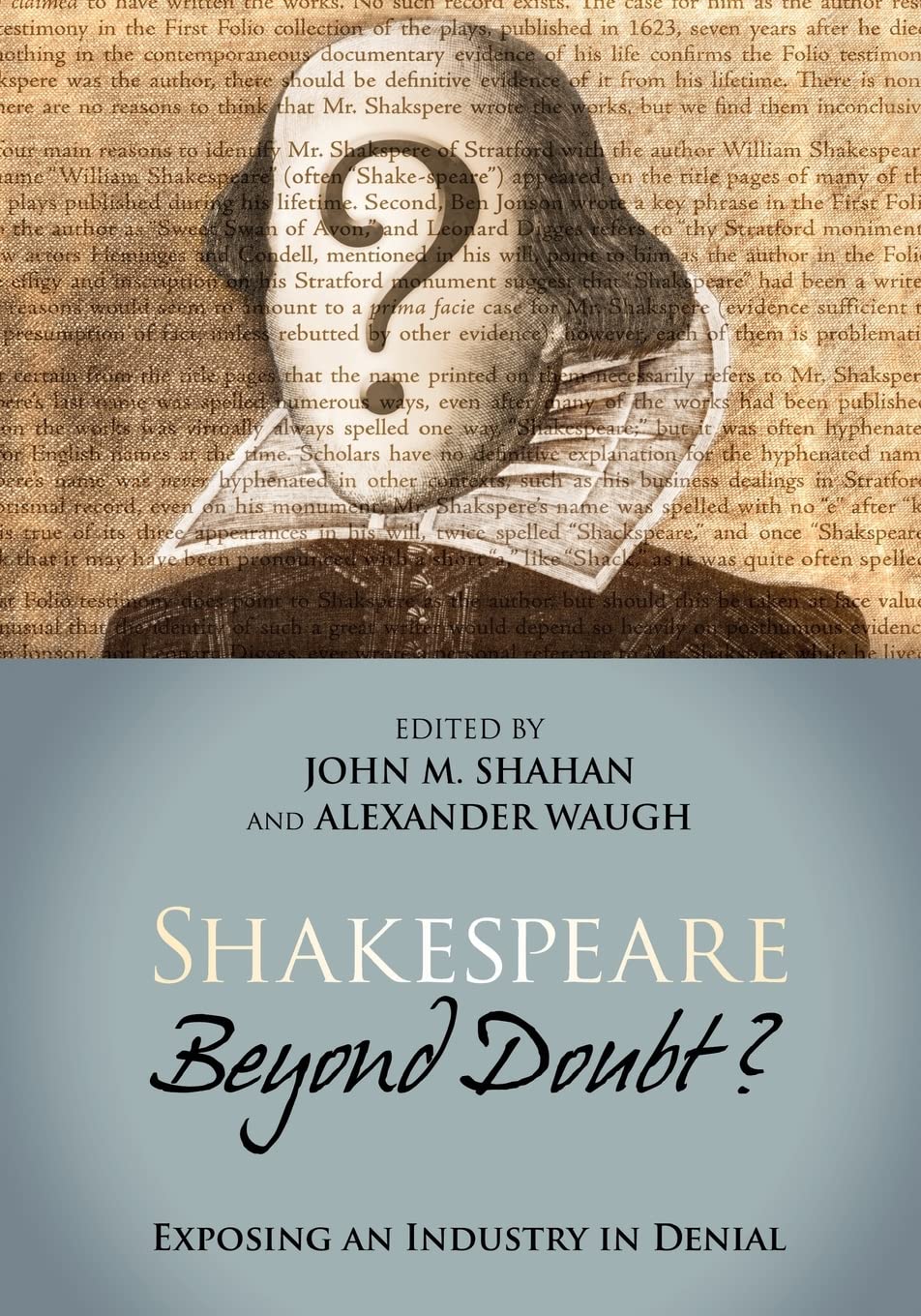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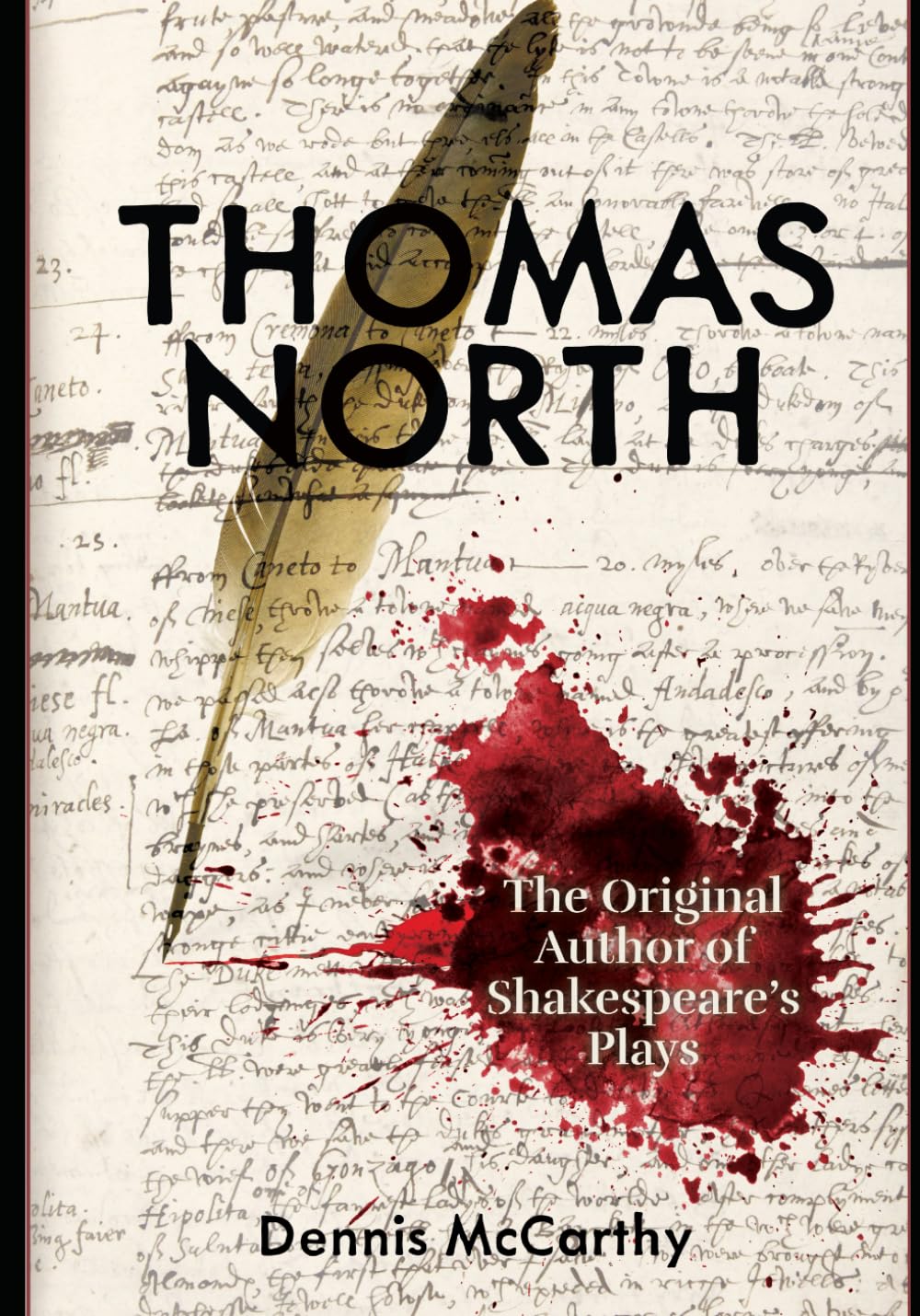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