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compactmag.com/article/the-great-feminization/
By Helen Andrews
2019年,我讀到了一篇關於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與哈佛大學的文章,它徹底改變了我過往看待世界的方式。文章的作者以筆名“J・史東”寫道,拉里・薩默斯辭去哈佛校長一職是美國文化的轉捩點。可以說,他的辭職就是整個“覺醒”(woke)時代的縮影,從薩默斯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被取消(cancelled)的境地,到最重要的是,是誰這麼堅持要置他於死地:女人。
我對薩默斯醜聞的整個經過算是有所耳聞。2005年1月14日,在一場題為“科學與工程領域人才多元化”的會議上,拉里・薩默斯發表了一些不太適合出現在公開場合的言論。在演講中,他聲稱硬科學領域之所以缺乏女性,部分是因為“高階人才本身的稀缺性”以及男女之間天生就存在著“並非社會化而造成”的興趣差異。一些在場的女教授們深感被冒犯,於是她們違反了會議內容不公開的規定,將薩默斯的發言透露給了記者。隨之而來的輿論譁然導致哈佛的教職員工最終不得不發起不信任投票,結果就是薩默斯必須辭職走人。
據那篇文章指出,這件事的重點並不在於那些女性取消了一位哈佛校長;真正的問題在於她們是以一種典型的女性化方式取消他的。她們選擇了訴諸情緒,而不是從邏輯上去辯倒對方。“當他開始談論男女之間的天生能力差異時,我幾乎快要喘不過氣,因為這種偏見使我感受到了生理上的不適,”麻省理工學院的生物學家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說道。薩默斯立刻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以澄清自己的言論,之後他又發表了第二份、第三份聲明,他的道歉更是一次比一次誠懇。有不少專家坦言,薩默斯關於性別差異的言論其實完全符合主流科學的觀點。然而,已經陷入歇斯底里的人們卻根本聽不進這些理性的聲音。
文章認為,“取消”這種行為本身就是非常女性化的,因為所有的取消幾乎都是女性發起的。取消文化實際上就是當女性在某個組織或領域中的人數達到了一定程度後,就必然會產生的現象。這就是“大女性化”(Great Feminization)理論,同一位作者在他後來出版的一本書中對此進行了更詳細地闡述:所有你知道的關於“覺醒”的一切,其實都只不過是這個國家正在逐漸走向女性化的寫照。
這個看似簡單的理論卻有著出人意料強悍的說服力。它確實揭開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少秘密。覺醒並不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衍生物,更不是因為後歐巴馬時代人們的幻滅而產生的。它只是女性將她們一直以來的行為模式套用在那些近年來才開始廣納女性的領域的結果。我以前怎麼會沒想到這一點呢?
或許是因為就跟大多數人一樣,我以為大女性化是早在我出生的很久以前就已經發生的事。比方說,當我們談起法律界中的傑出女性時,我們會想到第一位進入法院學習的女性(1869)、第一位在最高法院出庭辯護的女性(1880)或第一位在最高法院擔任法官的女性(1981)。
一個更重要的轉捩點是發生在法學院的女學生人數首次超過男學生,這是發生在2016年,或是律師事務所的女性助理人數首次反超男性,這是發生在2023年。當珊卓拉・歐康納(Sandra Day O’Connor)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時,女性法官的數量只有區區5%。如今,美國的女性法官人數已經來到了33%,而在拜登任命的所有法官中,女性更是佔據了63%。
其它許多領域都出現了類似的趨勢:20世紀60−70年代湧現了一批女性先驅;接著女性的比例在80−90年代不斷上升;到了2010年代或2020年代,性別平等終於大致實現,至少在年輕一代中是如此。1974年,《紐約時報》的所有記者中只有10%是女性。2018年,該報社的女性員工已經成為多數,達到了55%。
醫學院的女性人數在2019年實現了多數。同年,女性在全美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力中也佔了多數。2023年,有超過半數的大學教師都是女性。雖然女性目前尚未成為美國管理階層中的多數,但這一天可能很快就會到來,因為今天這個比例已經來到46%。所以,一切可以說是恰逢其時。覺醒運動興起的時間點,正好就是許多重要領域開始由男性主導轉變為女性主導的時候。
至於覺醒運動的內核就更是如此了。覺醒運動本身其實就是對女性特質而非男性特質的優先關照:同理心大於理性、安全大於風險、和諧大於競爭。其他曾提出過各自的大女性化理論的學者,例如諾亞・卡爾(Noah Carl)、博・魏納加德(Bo Winegard)和科里・克拉克(Cory Clark),他們都研究過這種女性化風氣對學術界造成的影響,並輔以紮實的數據證明了兩性在政治價值觀上的差異,舉例來說,一項調查發現71%的男性認為捍衛言論自由比維護社會和諧更重要,59%的女性則抱持相反的觀點。
最顯著的差異往往並不在於個體,而是反映在集體身上。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你每天肯定都會碰到一些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特例,但男女之間確實存在客觀的差異。如果你從統計學的角度來思考的話,就會發現這其實很合理。隨機挑選一名女性,她的個子可能會比另一名隨機挑選的男性要高。但隨機挑選十名女性,她們的平均身高卻不太可能高過另外十名隨機挑選的男性。群體數量越大,就越容易回歸統計平均值。
女性群體更傾向於達成共識與合作。男性群體更傾向於互相發號施令,但女性對彼此通常則只會提出建議和勸說。任何批評或負面情緒,即便非表達不可,也必須用層層的誇讚來包裝。討論的結果遠不如討論本身來得重要,重點是每個人都必須要參與其中。這種群體性別差異最明顯的一點就在於兩性面對衝突時的態度。簡單來說,男性往往更傾向於公開把矛盾講清楚,女性則傾向於暗中中傷或孤立她們的敵人。
芭里・韋斯(Bari Weiss)在她離開《紐約時報》的辭職信中講述了她的同事們是如何背地裡在Slack群組中辱罵她是種族主義者、納粹分子和偏執狂,而且——這恰恰是最女性的部分——“那些願意繼續親近我的同事,也跟著遭到了她們的排擠。”韋斯曾主動邀請《紐約時報》評論版的一位同事一起喝咖啡,結果那位經常撰寫種族議題文章的混血女記者卻完全不願與身為同事的她有任何來往。這顯然不符合最基本的職場禮節。而且,這也是一種非常女性化的行為。
男性一般比女性更能夠就事論事,而覺醒運動從許多方面而言恰恰是整個社會未能做到這一點的體現。在過去,一位醫生或許對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同時也知道不應該將自己的立場帶進診療室。如今,隨著醫學界變得日益女性化,現在有越來越多醫生會公開佩戴徽章和掛繩,以表達她們對從同性戀權利到加薩衝突等各種爭議話題的態度。有時她們甚至寧可讓政治凌駕於自己的專業,例如先前就曾有一群醫生為了力挺黑命貴抗議活動,即使這違反了當時的新冠防疫禁令,而硬說種族主義也是一種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有一本書帶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它是心理學教授喬伊絲・貝內森(Joyce Benenson)的《戰士與慮士:兩性的生存智慧》(Warriors and Worriers: The Survival of the Sexes)。她認為男性具有更適合戰爭的群體傾向,女性則具有更適合保護後代的群體傾向。這些可以追溯到史前時代的習性解釋了為何在貝內森引用的一項研究中,某個現代心理學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觀察到,當男性組的實驗者們被賦予了一項課題時,他們就會“紛紛開始踴躍發言,提出自己的意見,”然後“他們會興高采烈地向研究人員回報,他們已經討論出了解決辦法。”至於當女性組的實驗者們被賦予相同的課題時,她們卻會“禮貌地打聽彼此的背景和人際關係...伴隨著大量的眼神交流、微笑和輪流發言,”以至於到最後“似乎根本沒有人想要解決問題。”
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兩個部落之間的爭端,前提是雙方必須要能夠在爭端解決後言歸於好。因此,男性發展出了與對手和解的傾向,他們學會了與昨天仍在互相爭鬥的敵人和好。即使是在其他靈長類動物身上,雌性互相和解的速度往往也比雄性還慢。這是因為女性之間的衝突大多發生在部落內部,是為了爭奪稀缺的資源,所以她們的解決方式不是直接一決勝負,而是與對手展開一場默不作聲的鬥爭,並且往往沒有明確的結束時間。
所有這些觀察都與我對覺醒運動的觀察相吻合,但很快地,發現新理論所帶來的興奮就被一種深深的沮喪感給取代了。假如說覺醒運動真的是大女性化所造成的結果,那麼它在2020年的瘋狂大爆發就很可能只是未來的更多亂象的前奏而已。想像一下,當剩下的男性們繼續淡出那些塑造社會的職業,讓更年輕、更女性化的世代完全掌控了它們時,會發生什麼事。
覺醒運動造成的問題大小會因為具體的行業而有異。令人遺憾的是,今天的英語系幾乎完全由女性主導,但這對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其它領域的影響則更為明顯。你也許不是記者,但你仍然生活在一個《紐約時報》的報導將會決定公眾可以得到多少真相的國家。如果《紐約時報》變成了一家會因為公司內部的好惡而刻意不報導他們不喜歡的事實的報社(這在今天其實已經很嚴重了),那麼這毫無疑問將影響到每一位公民。
最令我擔心的當然是法律領域。我們所有人都需要一個運作良好的法律體系,坦誠地說,如果法律界也變成了女性佔多數,那麼法治將不復存在。法治並不僅僅是寫下一堆規則。法治意味著即使規則的結果觸動了你的心弦,或是與你從直覺上更同情的一方相違背,你也必須按照規則作出判決。
女性主導的法律體系或許會令人想起歐巴馬總統在2011年針對大學校園性侵害問題頒布的《第九條教育修正案》。這些程序受書面規則約束,因此從技術上而言,可以說它們仍是在法治框架下運作的。但它們卻缺乏我們的法律體系所固有的許多保障措施,例如與你的控訴者當面對質的權利、確認自己被指控了什麼罪行的權利,以及罪責認定應該基於雙方都能夠知道的客觀事實,而非只是其中一方在事後的主觀感受。這些保障措施之所以被省略,就是因為制定這些程序的人通常更容易同情控訴者,她們大多是女性,而不是被控訴者,他們大多是男性。
這兩種不同的理念在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任命聽證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碰撞。男性們的普遍看法是,既然克莉絲汀・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拿不出任何確鑿的證據證明她和卡瓦諾曾共處一室,那麼就不該讓她的性侵指控毀掉後者的人生。女性們的普遍看法則是,她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本身就是最充分的證明,參議院委員會應該要接受這一點。
如果法律界有一天真的被女性把持了,我想《第九條教育修正案》的速審法庭和卡瓦諾聽證會所帶起的風氣只會變得更加有恃無恐。法官們一方面會對那群受到優待的群體寬大為懷,另一方面卻對那群不受優待的群體嚴加懲處,這種令人擔憂的現象其實已經發生了。在1970年時,人們或許還不覺得女性大量踏入法律界會掀起什麼了不起的影響。但這種想法如今已經被證明是大錯特錯。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變革。
奇怪的是,政治光譜中的兩方都沒有否認這些變革正在發生。雙方唯一的分歧在於這些改變究竟是好是壞。妲莉亞・利茲威克(Dahlia Lithwick)在她的《正義女神:女性、法律與美國的存亡之戰》(Lady Justice: Women, the Law, and the Battle to Save America)一書中的一開頭就描述了2016年最高法院就德州墮胎法案進行口頭辯論的場景。三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Ginsburg)、索托馬約爾(Sotomayor)和卡根(Kagan)“無視發言時間限制,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斷她們的男性同事的發言。”利茲威克盛讚這是“女性司法力量的高光時刻”,它“讓美國的女性們得以一窺一個真正實現或者說接近性別平等的法律界應該是什麼模樣。”
利茲威克對這些女性們藐視法律慣例的態度充滿了讚揚,畢竟這些慣例是源自於一個充滿壓迫與白人至上主義的時代。“美國的法律體系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部為擁有財產的白人男性謀取特權的機器,”利茲威克寫道。“但它卻也是唯一可用的機器,所以你只能接受現狀。”那些將法律視為父權遺毒的人也必然只會將它當成工具。如果這種態度在我們的法律體系中成為顯學,那麼即使表面上看似什麼也沒變,但一場革命實際上卻已經發生。
大女性化革命的確可以稱得上史無前例。其它文明當然也曾經賦予女性投票權、財產權,甚至是讓她們繼承王位。然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文明嘗試讓女性掌控如此之多的重要社會機構,從政黨、大學到我們規模最大的企業。即使並非身居要職,女性們也往往能反過來掌控她們所身處的組織的基調,以至於男性CEO還必須在他的人力資源副總裁劃定的界線內行事。我們習慣了假定這些機構可以在這種全新的環境下繼續良好運作。問題是,我們做出這種假設的依據是什麼?
問題不在於女性是否天生不如男性,也不在於女性的互動方式有任何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女性的互動方式並不適合許多大型機構的宗旨。你當然可以擁有一個以女性為主的學術界,但它(就像今天大學裡的那些由女性主導的科系一樣)的宗旨將不會再是自由辯論與不受約束地追求真理。如果一個學術界不追求真理,那它還有什麼用?如果你的記者沒有那種不怕得罪人的精神,那他們還有什麼用?如果一家企業失去了桀騁不馴的冒險精神,變成了一個女性化的、自我內耗的官僚機構,那它又怎麼還可能有任何創新?
如果大女性化對今日的文明構成了威脅,那麼問題就變成了我們能做什麼來應對這個問題。答案取決於你認為究竟什麼才是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很多人認為大女性化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自然現象。女性終於獲得了與男性公平競爭的機會,然後事實證明她們更勝一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新聞編輯室、政黨和企業中有那麼多女性。
羅斯・多薩特(Ross Douthat)在今年接受右派出版人、網名“L0m3z”的喬納森・基珀曼(Jonathan Keeperman)採訪時就分享了他的看法,“長屋”(longhouse)一詞就是因為基珀曼而流行起來的,它被他使用來作為對這股女性化潮流的隱喻。“男人總是抱怨女人在壓迫他們。所謂的‘長屋’不就是一群男人在那邊哀嘆說他們根本競爭不過女人嗎?”多薩特問道。“也許你們應該振作起來,學會在21世紀的美國去進行公平競爭?”
這就是女權主義者的觀點,但她們錯了。大女性化並不是女性在公平競爭中勝過男性的結果,而是社會人為干預的結果,一旦我們停止干預,這股趨勢就會在一代人之內迅速結束。
最明顯的干預就是反歧視法。企業如果僱用的女員工不夠多就是違法。如果女員工數量不足,尤其是在高階管理職位,那麼這些企業就要吃上官司。因此,為了維持女性員工的數目,雇主反而得刻意為這些女性騰出她們本來不應該獲得的職缺和晉升機會。
雇主這樣做是完全情有可原的,否則後果可能會不勘設想。德士古、高盛、諾華和可口可樂等公司都曾因為被指控在招聘和晉升流程中存在對女性的歧視而惹上官司,並因此支付了數億美元的和解金。沒有任何管理者會願意讓公司僅僅因為性別歧視官司就賠上兩億美元。
反歧視法要求所有工作環境都必須變得女性化。1991年有一項里程碑式的裁決認定了造船廠牆壁上的性感海報會營造出一個對女性具有威脅性的環境,後來同樣的原則又擴大到包含了許多男性的尋常行為。數十家矽谷公司已經因為被指控存在“兄弟會文化”或“有毒的兄弟文化”而遭告上法庭,據一家專門處理此類訴訟的律師事務所表示,這些案件最後判下來的賠償金通常在四十五萬至八百萬美元之間不等。
女性可以狀告雇主,指控他們把工作場所變得像兄弟會一樣,但男性卻不能以雇主把工作場所搞得像蒙特梭利幼稚園一樣而控告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雇主會選擇迎合誰就很簡單了。所以,如果女性在現代職場中更成功,這真的是因為她們在競爭中贏過了男性嗎?還是說,這其實是因為規則變得對她們更有利了?
我們可以在大女性化隨著時間而不斷加深的趨勢中看見不少耐人尋味之處。一旦某個機構的性別比例來到50:50,它們往往就會超越性別平等,變得越來越女性化。自2016年以來,法學院的女學生比例一直在逐年上升;這一比例在2024年時已達到了56%。就連心理學這個曾經由男性主導的領域,現在也幾乎完全被女性佔據,如今有75%的心理學博士學位是被授予給女性。這些機構似乎都存在一個閾值,一但超過了它,它們就會踏上徹底女性化的不歸路。
這不是女性正在超越男性,而更像是女性將她們的規則強加於本來由男性主導的機構,並進而將男性拒之門外。哪個男人會喜歡在一個他身上的所有特質都不被歡迎的地方工作?哪個有自尊心的男性研究生會願意在學術界深造,即使他隨時有可能會因為直言不諱地表達異議或發表有爭議性的觀點而遭到同儕排斥?
今年9月初,我在全國保守主義大會上發表了一場與本文的內容大致相同的演講。本來我很緊張,畢竟這是要在公開場合談論大女性化的問題。就算是在保守派圈子裡,主張一旦某個領域的女性人數太多就會導致它無法正常運作,也仍然是一個非常具爭議性的觀點。所以我盡可能地以最客觀中立的方式表達我的觀點。出乎我意料的是,人們的反應非常熱烈。短短幾個星期內,我的演講在YouTube上觀看的次數就超過了十萬,更成為全國保守主義大會有史以來觀看次數最多的演講之一。
人們願意傾聽不同的觀點當然是好事,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去解決大女性化所帶來的危機了。大女性化在初期與末期各有不同的跡象,而目前的我們正處於中間階段,法學院的女學生確實是多數,但聯邦法官仍主要是男性。或許這股性別轉變風潮將在數十年來自然迎來它的結局。有很多人認為覺醒運動實際上已經到頭了,它已被社會風氣的轉向所終結,但如果覺醒運動真的是整個國家女性化的結果,那麼只要國家本身沒有做出改變,覺醒文化就永遠不會消失。
作為女性,我自然十分感激自己有從事寫作與編輯工作的機會。值得慶幸的是,我認為要解決大女性化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將女性逐出職場。我們需要的只是讓規則重新變得公平。我們表面上鼓勵選賢與能,實際上卻將不選擇女性認定為違法。我們應該讓這個制度變得真正任人唯才,而不是徒有虛名,然後來看看結果會是如何。我們需要重拾男性化的職場文化,撤除人力資源主管的否決權。我認為屆時人們將會驚訝地發現,今天我們這個社會的很多女性化現象,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制度上的變化而導致的,例如人資制度,而這些變化又是由法律變化所導致的,所以它也同樣可以通過法律來扭轉。
畢竟,我不僅僅是一個女人。我還是一個抱持著與他人不同意見的人,如果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迴避衝突、只想追求和諧,那麼就不會有我這種人發聲的空間了。我也是幾個兒子的母親,如果他們被迫在一個女性化的世界中長大,他們將永遠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我——與我們所有人——都深深依賴法律體系、科學研究和民主政治等支撐美國生活方式的制度,一旦這些制度無法再履行它們的職責,最後受苦的只會是我們每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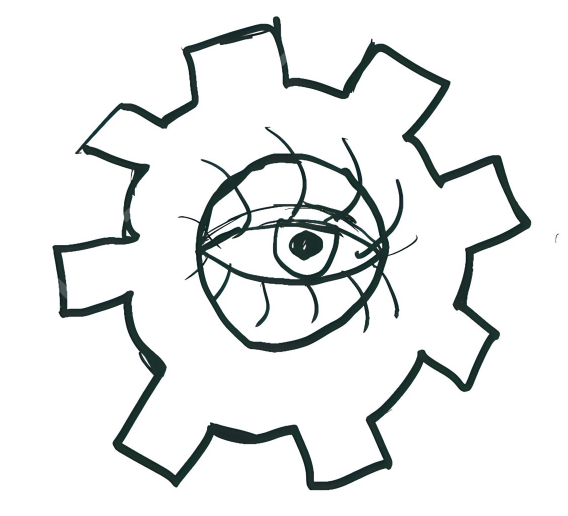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