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the-ancient-art-of-memory-the-modern-science-of-dreaming
BY ERIC WARGO
我的年紀夠老了,我還記得在我們發現鳥類其實就是從恐龍演化而來以前的那段日子。就跟很多20世紀70年代的孩子一樣,我曾經覺得恐龍是世界上最酷的東西,這部分是因為牠們距離我們如此遙遠,又滅絕的如此徹底。但後來古生物學家才發現,原來這些古老的怪物一直都在我們身邊,我們從窗外就可以聽見牠們的聲音,這一發現既令人震驚卻也多少讓人感到有些寬慰。
許多“古代智慧”其實就像是這樣。我們或許以為早已被遺忘的傳說,實際上只是變成了不同的模樣。在一些情況下,它甚至仍然存在於我們最不容易起疑的地方或偽裝中。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一項古老的技巧,三十年來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讀書的時候它總是能派上用場:古騰堡時代之前的學者和演說家們的驚人記憶術。
如今還知道這項技巧的人不多了,但我很幸運地在20世紀80年代的科羅拉多大學課堂上認識了它。當時一位老師推薦我閱讀弗朗西絲・耶茨(Frances Yates)的《記憶的藝術》(The Art of Memory,註1),還說這是他讀過最發人深省的一本書。這聽起來是個不錯的建議——於是我立刻去大學書店買了一本。那晚我在家裡翻著這本書,我感覺自己踏入了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且它不僅僅關於心靈與歷史,也適用於電影、視覺藝術、文學以及心理學。這真的就像是俗話說的醍醐灌頂,是當之無愧的改變我人生的閱讀體驗之一。
我們今天喜歡談論“閱讀體驗”,但對古代世界與中世紀——也就是耶茨研究的時代——的人們來說,書本是很珍貴、稀有的東西,如果你是一個識字的人,讀書絕不是可以囫圇吞棗和消遣解悶的小事。一位旅行學者就算有幸能在某位富裕贊助人的書庫裡研究一本稀世之典,往後恐怕也再不會有機會接觸這本書了。即便是僧侶或神父閱讀《聖經》的機會也十分有限。但令人驚訝的是,古希臘、羅馬或中世紀的博學之士卻能將許多書籍的內容倒背如流;彷彿他們的頭腦就是一座圖書館,裡面整齊地擺放著他們在做學問或旅行的過程中有幸得到、閱讀和研究過的每一本書。在跟人辯論的時候,哪怕手上一張紙都沒有,他們依然能夠流利地引經據典、背誦長篇文章。
這個技巧其實很簡單:如果你想記住一個想法或事實,你所要做的就是將其拆分成好幾個部分,用它喚起你聯想的其它東西來逐一替代每個部分,然後將這些東西重新組合成令人難忘的小圖像或畫面。若想記住整場演講或佈道的講稿,你需要在想像中沿著熟悉或有深刻印象的環境,例如你的家或公共廣場,來有序地“擺放”這些圖像。然後等到真的要發表演講的時候,你要在同一個空間中進行一次精神漫步,按序瀏覽每一個生動的圖像,“取出”你種植在它們身上的事實或想法。
不妨舉一個例子:想像一個大學生需要背起一長串的歐洲史好應付考試。發下來的講義已經列出了考試中可能出現的人名、年代與重要事件,例如“諾曼人於1066年入侵英格蘭”。單就它們本身而言,諾曼人、英格蘭、1066年這些赤裸裸的事實對這個大學生來說可能沒有什麼甚至毫無意義——她根本不知道諾曼入侵者長什麼樣;就跟大部分的數字一樣,1066也沒什麼特別的;更何況她可能從來沒去過英國,當然她肯定會通過電視和雜誌而對威廉王子與他的妻兒有一些印象。不過,假如她幸運的話,我們假設這個學生曾經在某個時候跟她的老師或助教學過記憶術的基本技巧:盡可能運用所有突發奇想的、不講理的、最個人的聯想,並從中構築出一幅心理概念圖。
因此,假設我們這位大學生剛好很迷60年代的搖滾樂,而且巴布・狄倫的每張專輯她都滾瓜爛熟。所以,1066年可能會讓她聯想到1966年,即《金髮尤物》(Blonde on Blonde)發行的那一年。雖然她也許不知道真正的諾曼人長什麼樣,但她正好有一個叔叔就叫諾曼。一個聰明的、精通記憶術技巧的學生在埋首苦讀時不會刻意去壓抑這種荒謬的、看似無關緊要的聯想,而是會任由她的玩心繼續聯想下去,甚至是開始打扮這些聯想——例如,她可以想像她的叔叔突然有了一頭金髮(在現實中他是黑髮),穿著廉價的達斯維達式斗篷與面具(“穿著維達裝”〔in Vander〕剛好音同“入侵者”〔invader〕,“廉價面具”而不是完整的頭盔則讓我們依然能看見他的金髮),然後用他的光劍將威廉王子劈成兩半。至於其它要熟背的事件和年代,她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技巧繼續創造出更多類似的、奇怪的,以及是的,看起來有點白癡的圖像,然後運用想像力在隨便一條她熟悉的道路,例如從她的宿舍走到歷史教室的那段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放上一個圖像。
我跟你保證,她這麼做之後一定能通過考試。
當耶茨剛開始撰寫她那本書的時候(很巧也是在1966年),她其實還對此抱有懷疑的態度:雖然這項技巧似乎真的蠻厲害的,而且像佐丹奴・布魯諾這樣的赫耳墨斯主義思想家也曾親自拍胸脯保證它非常有用,但這些都不足以使她信服。她認為這種用想像新的圖像來記住事情的方式實際上比直接死記還要更費力。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對記憶心理學的研究卻恰恰解釋了,為什麼這種古老的方法確實比死記硬背更有效。
記憶是通過聯想來運作的——在其中各式各樣的資訊並不是透過邏輯,而是根據它們的形式或聽起來是否相似(例如雙關語和押韻)來產生聯繫;它們可以依照任意的方式排列,像是一張清單或一首歌;甚至是當我們在學習它們的時候正在做什麼、在哪裡或有什麼感受都可以形成聯繫。當我們從自己的心靈中翻箱倒櫃尋找某個資訊時,我們會通過快速追蹤一些非常私密且具有異質性(idiosyncratic)的聯繫來找到我們需要的東西——例如我們早餐吃的是什麼,而這又會讓我們聯想起當時我們正從廣播中聽到的一條特別有趣的新聞是什麼。
與直覺相反,這種不合邏輯的聯想反而具有最好的記憶效果,因為它使我們能通過許多替代路徑來迅速找到需要的資訊。你的腦皮質是一個巨大的多維網路,它包含了數不清的非邏輯聯繫,而這些聯繫更是橫跨了你一輩子的人生經驗。
當那個大學生想像她的叔叔穿著達斯維達裝怒斬威廉王子的畫面時,除了諾曼人入侵的歷史事實之外,她其實並沒有真的創造出任何需要她記住的新事物;她所使用的都是本來就已經存在於記憶中的東西,它們自然而然地通過聯想從她的腦海中浮現,並通過稍微的扭曲產生互相聯繫,就像你扭彎兩條電線的末端來使它們互相連接。可以說這是一種好玩的心理藝術創作。要編造這樣的圖像不需費吹灰之力,記住它們也不需要任何努力。由於它們實在太荒謬了,它們幾乎立刻就會被自動記住。
像愛因斯坦這些現代天才的傳記則告訴了我們,儘管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這麼做,但他們其實就是在使用記憶術,即像對待玩具和材料一樣把玩資訊,而不是用蠻力將它們硬塞進腦袋裡。
皇家大道
我常說,研究古人的智慧總是能給人驚喜——我自己已經練習記憶術十幾年了,而它也帶給了我無以計數的回報,特別是彷彿自己掌握了一個千古秘密的興奮感。然而,更令人欣喜的還是發現這種古老的智慧實際上依然存在於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沒有可能我們所有人其實都是像布魯諾一樣高超的記憶魔法師,只是我們從來沒有發現?想一想:諾曼叔叔穿著達斯維達裝劈開威廉王子,這不正是我們每天晚上在夢中都會看見的那些超現實主義景象嘛。這是否意味著,做夢與記憶術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
夢境的光怪陸離使古往今來所有文化中凡是有理性的人都同意,這些發生在夜間的幻覺與遭遇應該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具有某種重要的意義。1900年,佛洛伊德在他的鉅著《夢的解析》(註2)中將夢具有象徵意義這個常識與當時新興的心理科學結合起來。他認為夢境是我們平時被壓抑的慾望在通過象徵性的方式進行抒發。他這個了不起的想法奠基於一個觀點,即潛意識如果一直藏著秘密會讓我們生病,或至少是讓我們變得心煩意亂和悶悶不樂,直到這些秘密被好好一吐為快。所以他說,夢境是通往潛意識的“皇家大道”。
然而,很難用科學對佛洛伊德的理論進行驗證,並且假設夢境確實是某種慾望的展現,這些佛洛伊德式的夢境也很容易會因為病人或醫生的主見而被曲解成任何含義。“抒發慾望”的想法本身亦略顯牽強,就連佛洛伊德本人都在他晚年研究退伍軍人的夢時承認了這一點:他們有些人的夢境根本一點也不快樂——且絕對沒有向我們呈現出任何內心深處的渴望。出於這些及其它原因,20世紀下半葉的心理學家大多反對佛洛伊德,並選擇從完全不同的思路下手,尋找做夢的生物學基礎。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極力否定任何承認某種神秘性存在的想法,像是夢境包含象徵意義、你可以像解讀一首詩那樣來解夢,或是夢可以像間諜破譯密碼那樣來被進行解碼。
幾十年來腦神經科學家已經提出了許多試圖解釋我們為什麼會做夢的理論,通常都十分枯燥——例如,它們只是隨機的大腦雜音,或是它們的作用是要以某種方式使我們做好應對威脅的準備。但從各種不同來源累積起來的間接證據卻表明,夢可能自有它的某種內在邏輯,而且這種邏輯與強化舊記憶、創造新記憶有關。
在實驗室的實驗中,接觸過新資訊的人在“入睡”後會比沒有入睡的人更容易記得它;研究還發現,在睡眠期間,白天學習的複雜資訊會被簡化,好變得更容易理解。出生時最需要依賴父母的動物,例如鳥類、人類及其他很多哺乳類動物,都比爬蟲類動物等一出生就已經十分成熟的物種在睡眠的時候有更多的快速眼動期(REM,換句話說,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動物所需要學習的東西越多,其大腦在晚上就越活躍,所做的夢也就越多)。對囓齒動物的研究則表明,在白天的探索與學習過程中被啟動的大腦區域會在睡眠期間被再次喚醒。我們還知道,長久以來即被認為對產生新的記憶有重要作用的海馬體在我們入睡時也會特別活躍。
目前更有越來越多證據表明,我們白天中的重要事件和遭遇往往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進行消化的,尤其是REM發生的那大約兩個半小時,那也是我們的夢境最精彩的時候。因此,說夢中的奇異景象是對這種夜間記憶過程的直接反映是有道理的。可是,夢境的內容是如此離奇,又往往跟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沒有絲毫關聯,這一事實一直以來總是困擾著無數想要弄清夢境與記憶之間的確切聯繫的嘗試。
這個問題有很大一部分其實在於科學家們實在太忙(且太死腦筋)了,以至於他們連瞧圖書館裡的其它非科學類書籍一眼都不願意。直到2013年,曼徹斯特商學院的一位名叫蘇・盧埃林(Sue Llewellyn)的心理學家才意識到,文化史學家所熟悉的古老記憶術很可能正是夢境之謎缺失的那一塊拼圖(註3)。她發現夢境的怪異內容似乎跟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事件有著同樣的關係,好比諾曼叔叔穿著達斯維達服劈開威廉王子,就對應著1066年諾曼人入侵的歷史事實。她認為夢其實就是我們在睡覺時開始自動施展古老的記憶術。它們並不是真的將我們白天時發生的事件重新再演一遍。相反的,它們是在向我們呈現我們與這些事件的私人聯繫。我們的大腦通過每天晚上製造這些聯繫,來將最近發生的事情與更久以前、更優先的事情以及更古老的記憶連接起來。
向前邁進
新的夢境記憶理論很好地解釋了幾個關於夢的陳年常識,像是為什麼它們經常涉及性、為什麼它們經常包含巧妙的俏皮話和雙關語,還有為什麼它們總是很難記住。
佛洛伊德因為夢中有太多性和暗示性的生殖器象徵主義而斷定它們一定是我們被壓抑的慾望。但如果夢真的有促進記憶的作用,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說春夢之所以如此常見,純粹是因為這種令人血脈噴張的情緒往往更容易被記住而已。這是關於記憶的一個眾所週知的道理。事實上,正是出於這個緣故,性是古代記憶術中的重要環節。大部分的老師對這一點往往不願多談,但一位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術大師拉文納的彼得(Peter of Ravenna)卻坦率承認,性感的圖像就是他的秘密技巧之一:“我常常會用姚窕淑女的圖像來填充我的記憶,這麼做有助於強化記憶力。”他說。“如果你想快速記住某件事,就把最美麗的處女圖像塞進你的記憶裡,女性的形象最能夠刺激記憶力...”(註4)
在我們今天這個更加開明的時代,你當然可以選擇用“任何符合你性癖的東西”來取代“最美麗的處女”。重點不在於這個性幻想對象是不是女性,而是對你而言這個對象能不能成為最好的記憶誘餌。
夢的另一個常見的特徵是精彩的文字遊戲,尤其是雙關語。舉例來說,我的一個朋友曾跟我分享一個令人不安的夢,夢中她參加了妹妹舉辦的晚宴,結果她卻驚恐地看到妹妹的頭出現在開胃菜的盤子上。我知道我的朋友有點嫉妒她妹妹的成就,後者不僅已經結婚還有了房子(而我的朋友依然人財兩頭空),所以這個夢其實一點也不神秘:它只是在說,她妹妹領先(ahead=a head〔一顆頭〕)了。當我向她說明這一點時,她驚訝得下巴都要掉了下來。
夢中的雙關語常常涉及多種聯想,並且它會調動我們的所有感官,而不僅僅是著重於單詞的發音而已。有時是視覺上的刺激,有時是情感和多種感官上的一語雙關,有時它也會與現實生活中的情況形成某種“押韻”。當然,幽默的文字遊戲也是記憶術的核心技巧:諾曼叔叔是對諾曼人的一語雙關,讓諾曼叔叔穿上達斯維達裝也是對入侵者的一語雙關。
佛洛伊德認為,多層次的雙關語有助於夢境用很少的東西來傳達更多的道理——這就跟講笑話一樣——這同樣與記憶理論是完全一致的。佛洛伊德可能會說,我朋友的夢境很生動地說明了她妹妹“領先”的事實,同時又表達了她希望妹妹的成就只不過是我朋友自己一定也能迎頭追上的前奏曲(所以才會是開胃菜)而已——然後也許其中還摻雜了一點點兄弟姐妹之間的“死亡願望”。從一個夢境中發散出來的各種聯想鏈反映了大腦聯網網路的多條路徑,這些路徑讓不同的想法——在這個案例中是“我有點恨我妹妹,因為她比我更優秀”——在做夢者的腦海中保持活力與彈性。
可是,如果做夢的目的是為了強化記憶,為什麼夢卻總是這麼難以記住呢?我們每晚都會做大約兩個半小時的夢,但每天早上就算幸運也只能記得少許的部分,如果真的還想得起的話。除非你趕快把它們寫下來,否則就連這些部分也會在你開始吃早餐後迅速褪色。仔細想想,這其實並不奇怪:因為我們真正應該記住的是昨日的記憶。昨晚被製造出來的夢就像是胃在消化食物並將其轉化為身體所需的營養一樣。昨天的回憶現在變得比睡前更生動了,這是因為做夢活動在我的大腦中創造並強化了通往這些記憶的道路。也許我們本來就沒必要去看到或記住我們夢裡的內容,這就像我們沒必要去看到我們肚子裡的東西...如果我們堅持要這麼做,反而可能才會出問題。
我喜歡把夢想像成建築工地的腳手架和起重機:一旦施工完畢,它們就會迅速被拆除——然後就這麼沒了。在記憶術中被創造出來的圖像也是如此:我可以現在可以不用看我的卡一眼就在電話中報出我的信用卡號碼,而我已經完全不記得幾年前被我用來記住它們的那堆奇怪圖像——我依稀記得似乎與一艘帆船和一條巨大的舌頭有關。我沒記錯的話還有一些裸體的人(有關記憶術的具體指南,還有幫助記憶的簡單數字技巧,請參與我的另一篇文章《記憶術:為什麼它是有史以來最酷的發明及為什麼你應該在今天學習它》)。
喚醒童年
現在試著與你內心中的夢想家進行對話吧。早上醒來後請盡可能記錄下你的夢——記錄下每個人物、物體與情節,以及你注意到的每個特別或奇怪的細節。然後,對於每個比較不尋常的元素,花點時間記下它讓你想起的第一或第二件事或情況。要誠實的想,但不必強求。透過片刻的自由聯想,一個看似荒謬絕倫的夢中元素卻會出乎意料的指出你最近在生活中碰到的問題或關注的事情,然後它會繼續揭示出更多驚人的聯繫,通往遙遠的記憶、當下的流行文化還有被你遺忘在精神閣樓裡的各種東西。僅憑一個夢,你就可以寫滿一頁又一頁的日記了。
夢中思想往往是如此的狂野又精彩,著實超出了我們的日常經驗想像,以至於沒有紀錄自己夢境習慣的人常常很難接受他們看似魯鈍的頭腦居然可以創造出這些堪比莎士比亞的故事。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夢在過去常被認為是神靈的啟示,又為什麼今天的許多人都無法記得他們的夢——因為我們透過夢境所展現出來的幽默與天賦,完全不符合我們平時總是加諸於自己身上的認為我們是怎樣或應該是怎樣的一個人的成見。但我們沒有理由任由自己被這些成見束縛;創造出這些夢境的正是我們的大腦,也就是我們自己。
另外不要把你的造夢工作侷限在做夢上。練習記憶術同樣有助於養成做夢的習慣。它可以強化靈活性與創造力,讓你迅速變成一個驚人的智多星。人們會非常好奇你究竟是怎麼知道這麼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夠將夢境中的那種童心未泯的思維重新帶回你的日常生活,然後你就可以用各種創造性的方式將其應用在生活中。只需稍加練習,任何人都能夠學會這個好玩的學習技巧,並且成為一位記憶術大師。
童年從來沒有真的消失,就像恐龍從未真的滅絕。它只是潛伏到了檯面下。通過夢境和記憶術,你可以再次將它喚醒過來。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Frances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Pimlico, 1996 (1966)
2.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Avon Books, 1965 (1900)
3. Sue Llewellyn, “Such stuff as dreams are made on? Elaborative encoding, the ancient art of memory, and the hippocampu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ume 36, Issue 06, December 2013, 589-607
4. In Paolo Rossi, Logic and the Art of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2
埃里克・沃戈(ERIC WARGO)是一位住在華盛頓特區的科學作家,並擁有人類學博士學位。他經營著一個討論未來主義、科幻小說和超自然現象的部落格www.thenightshirt.com。想要聯繫他可以通過eric.wargo@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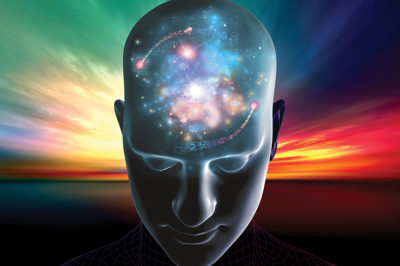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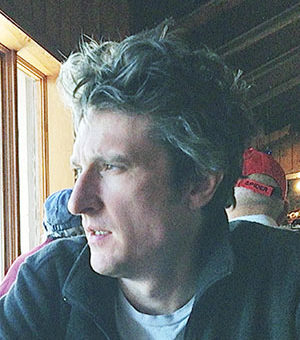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