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rescuing-the-bible-from-literalism
BY RICHARD SMOLEY
“世界,”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寫道:“是事實(facts)的總和,而不是事物(things)的總和。”這話說得確實在理,但是事實也有很多形式,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那種硬事實只不過是其中一種且並不總是最重要的形式而已。
西方盛行的實證主義思想可能會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對實證主義來說,事實只有已發生了與沒有發生兩種可能,一件事實是真是假也只能通過這一標準來予以判斷。然而,這其實不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立場。這個標準放在歷史探究、新聞報導甚至是科學研究(儘管20世紀的物理學經常得出有違常識的發現,令人不由得對此重新深思)上也許確實有幾分道理。但是在靈性世界中,儘管事實當然也很重要,但那與我們一般所理解的事實卻不太一樣。忽略了這一點,就很容易會犯下把兩種不同意義上的事實混為一談的誤解。
傳統基督教就經常犯這個錯誤。事實上,它從一開始就因為對直譯主義的堅持而陷入了矛盾:《聖經》不但千真萬確,而且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這代表這些真理肯定都符合史實,因此《聖經》對過去歷史的記載絕不可能有錯。至少在一開始,基督教靠著這種立場在古代世界迅速獲得了成功。到了公元世紀初左右,希臘-羅馬文明早已對自己原有的神話失去了信心,人們最終接受了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聖經》,理由不只是因為它似乎傳達了神聖的真理,更是因為它號稱準確紀錄了過去的歷史。
可是自從啟蒙運動以降,這種說法反倒成了包袱,而不再是推銷信仰的廣告了。過去兩百五十年來有無數信奉基督教的學者嘗試驗證《聖經》的科學性與史實性,結果可以說是令人失望。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流逝,《聖經》已有越來越多的內容開始被質疑根本與史實沾不上邊。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股風潮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英國科學家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在1830-32年發表了他蔚為經典的《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他在書中提出不同岩層顯示出的地質變化,根本不可能在地球按照《創世紀》所說的只有短短六千年的歷史裡完成,而是顯然需要更長的時間。之後另一位名氣更加響亮的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主張地球上的動物並不是一位造物主在公元前4004年的某天的創造,而是經過他稱之為“自然選擇”的漫長過程後所造就的結果(當達爾文剛完成他的巨著《物種起源》時,他還先把它送給萊爾過目以徵求意見)。
《聖經》的史實性受到挑戰
近幾十年來,考古學甚至對《聖經》中的一些看起來至少應該含有一點史實成分的段落都提出了質疑。舉例來說,僅僅一代人以前的學者大多都還接受出埃及的史實性,當然其中關於神蹟的部分另當別論,總之這場民族大遷移應該是確有其事。但後來情況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以色列・芬克爾斯坦(Israel Finkelstein)和尼爾・希爾伯曼(Neil Asher Silberman)在他們出版於2001年的《揭露聖經》(The Bible Unearthed)中總結了最新的發現,其中沒有任何考古證據可以證明過去真的發生過出埃及這回事。據他們指出,歷史上第一次提到以色列這個名字的是來自公元前1207年法老麥倫普塔(Merneptah)時代的一塊石碑。雖然這大致相當於傳統上認為出埃及發生的年代,但那塊碑文記載的卻不是以色列人的出逃(也不是被驅離),而是麥倫普塔成功征服迦南,令以色列人不得不俯首稱臣。總而言之,由於當時的迦南也是埃及的領土,因此以色列人從埃及逃往迦南其實根本沒有意義;麥倫普塔只要一揮手,就可以讓鬧事的省份再也無法造次。
相反的,芬克爾斯坦和希爾伯曼主張出埃及的故事實際上是人們對希克索人(Hyksos)——這是一群曾在公元前1670-1570年統治埃及、後來被埃及人驅逐的閃米特人——留下的記憶逐漸被以訛傳訛後形成的結果。我們所熟悉的出埃及故事成型於公元前7世紀,當時耶路撒冷和猶太人的國族意識形態才正開始萌芽——而他們的鄰居埃及則是一個強盛富庶又窮兵黷武的大國。
其他學者也提出了同樣具有顛覆性的見解。據英國《聖經》學者瑪格麗特・巴克(Margaret Barker)在她的《偉大的天使》(The Great Angel)中指出,以色列人最初曾崇拜過一位名叫亞舍拉(她有時也被稱為后赫瑪〔Hokhmah〕,意為“智慧”)的女神,她被認為是耶和華的配偶,耶和華本人也被人們視同於迦南的至高神-厄爾(El)化為以色列人的民族守護神後的變體。巴克認為約西亞王(King Josiah)發起的著名的申命改革——約西亞藉此清除了聖殿中供奉的其他神祇,從此確立耶和華獨一無二的地位(《列王記下》22-23)——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竄改,它毀掉了歷史悠久的傳統,並試圖以“耶和華獨一神論”來取而代之。這場運動最終成功改變了經歷巴比倫之囚後的猶太教,同時它也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篡改了猶太教過去的歷史。
人們還可以對《聖經》其餘的內容提出類似的議論。自從阿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大聲疾呼要“尋找史實上的耶穌”以來已過了兩個多世紀,但這方面的進展卻依然乏善可陳。大多數學者都相信《新約》中記載的耶穌故事是各種神話與傳說的東拼西湊,但對其中有哪些是、哪些不是原創,他們也還在爭個沒完。由一群自由派《新約》學者成立的耶穌研究會(Jesus Seminar)因為主張福音書中的記載幾乎完全與史實上的耶穌無關而引起了軒然大波。令人震驚的是,這甚至不是什麼新的論調:從19世紀開始就已經有很多德國的《新約》學者做出了相同的結論。甚至還有一種更激進的觀點認為,歷史上根本沒有耶穌這個人,他的故事純粹只是流傳在古代世界的眾多死後復活神話的猶太版本而已。由於基督的一生缺乏相關的考古證據,而且也難以指望文獻證據(沒有任何一本福音書、正典或偽經曾標榜自己是第一手的目擊記錄),所以這種主張即使再怎麼極端也很難被直接反駁。
作為寓言而非歷史的《聖經》故事
既然如此,我們還有必要把《聖經》當做歷史來看待嗎?毫無疑問仍有些人會這麼做。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曾說過,在福音派基督教中,光是傳道人對著聽眾揮舞手上的軟皮《聖經》就足夠了,但顯然並不是所有人願意買帳。其他人可能會被另一種方法所吸引——這是一種同樣歷史悠久、甚至可能還更加悠久的方法。按照這種方法的詮釋,《聖經》從來都不應該被從字面上去理解,反而真正有見識的人會從中發掘出更深刻的含義。
這種立場可以一直追溯到基督教誕生之初,與狹隘的字面直譯主義幾乎是同時並存。諷刺的是,這正是使得基督教在過去得以與猶太教劃清界限的原因。當時新生的基督教往往必須對《舊約》採取寓意解經,以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論述。比如使徒保羅說過這麼一段話:
“因為律法上記著,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使女生的,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是憑著應許生的。
這都是比方: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
一約是出於西奈山,生子為奴,乃是夏甲。
這夏甲二字是指著亞拉伯的西奈山,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兒女都是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們的母。”
(《加拉太書》4:22-26)
所以保羅的意思是,亞伯拉罕和他兩個兒子的故事其實是在隱喻猶太人與基督徒的關係。長子以實瑪利是夏甲,即“使女”所生,他代表的是那些被摩西的律法所“束縛”的猶太人。次子以撒是“自主之婦”撒拉所生,他代表的是不必再頑固恪守摩西律法的基督徒。因此,這是一個“寓言”故事。
第一個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寓言”(它的希臘語是allegoria)的權威——也是第一個使用這種方法來對《舊約》進行解經的人——是一位與耶穌、保羅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哲學家:亞歷山卓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前20-50)。儘管斐洛從未提及耶穌或保羅,《新約》也不曾提到斐洛,但斐洛對基督教的影響再怎麼誇大都不為過。姑且舉一個例子,正是他首先使用希臘語邏各斯(logos,一般被翻譯成“道”〔word〕)來表示我們意識中的那股創造性、結構性力量,進而提出整個世界都是按著這個原理所造。斐洛的觀點在公元1世紀的猶太教中十分盛行,後者經常將邏各斯奉為deuteros theos,亦即“第二神”。基督徒也採用了相同的神學觀,尤其是《約翰福音》,這卷書開篇的第一句話便是“太初有道”,這幾乎就是斐洛的思想。當然,斐洛從未像基督徒那樣直接把邏各斯等同於耶穌,隨著基督教的觀點逐漸散播到整個古代世界,反倒是猶太人轉而排斥起了邏各斯的概念。
總之,斐洛的做法就是從寓言的角度來理解《聖經》。以下是斐洛對《創世紀》的解讀:
“‘到第六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會相信世界真的是在六天內或是在時間中被造...但是...說世界不是在時間中被造恰恰是正確的,因為是首先有了世界,接著才有了時間...因此,當摩西說:‘神在第六日完成了祂的工’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他說的並不是真的六天,而只以六這個完美的數字來作為比喻。”
後面斐洛又繼續解釋他所謂完美的數字是什麼意思。顯然,這遠比純粹從字面上去解讀、相信世界是在六天之內被創造的觀點要更深邃也更奧妙。
基督教神學家中最推崇斐洛的是3世紀的早期教父俄利根(Origen)。然而,俄利根甚至走得比斐洛還遠,他迫不及待地想駁斥針對那些看似完全有違理智的經文的字面詮釋。下面是俄利根對《創世紀》的評論:
“誰要是真的相信上帝曾扮演園丁在伊甸園的東邊開闢了一座花園,又栽種了一棵看得見摸得著的生命之樹,然後任何人只要吃了它的果子即得永生,誰就是無可救藥的傻子;還有吃另一棵樹的果子就會變得能夠‘分別善惡’?據說上帝會在‘天起涼風的時候’到園裡散步,然後亞當就在那裡的一棵樹下休息,我不覺得有人會把這些段落當真,雖然這些事未曾發生,但它們以隱喻的方式揭示了某些奧祕。”
俄利根也沒有漏掉福音書或使徒們的著作:“即使呢,”他寫道:“這些作品訴說的故事也不全都是真的,真實發生過的事被與未曾發生過的事交相陳述;就連律法和誡命都沒有宣告過有哪些事是可信的。”
這幾乎就像現代人才會有的態度——但這些話卻是出自一位生活在3世紀的早期教父之口。俄利根認為《聖經》本身有三個層次的含義(分別是屬肉、屬魂、屬靈的層次,對應了早期基督教對人類本質的三重劃分)。這種觀點對後世產生的影響是無以估計的。學者貝里爾・史莫利(Beryl Smalley)就寫說:“要撰寫一部俄利根主義者如何影響西方文明的歷史,就形同於是撰寫一部西方文明的(《聖經》)釋經史。”
到了中世紀,俄利根的三層經文含義觀已經被擴展到四層。分別是字面詮釋、寓言詮釋、道德詮釋和“奧義詮釋”(anagogical)或稱神秘詮釋。但丁就在一封寫於14世紀初的信中向坎・格蘭德(Can Grande)解釋了他對《出埃及記》的詮釋:
“如果從字面的角度去理解,這卷書是在談論摩西時代的以色列子民如何從埃及流亡;如果從寓言的角度去理解,這卷書是在暗示基督對我們的救贖;如果從道德的角度去理解,這卷書是在陳訴我們的靈魂從與罪惡的鬥爭與苦難中找到恩典的過程;如果從奧義的角度去理解,這卷書是在講述靈魂從墮落的奴役中解放,奔向永恆榮耀的自由。”
雖然所有這些玄之又玄的解讀法被冠以了不同的稱呼,但它們基本上都可以被稱作寓意解經法,因為它們都不著眼於字面或史實含義。
俄利根對揭露《聖經》的隱藏含義倒是顯得相當支吾其詞(“揭露這些真理與被隱藏的含義,應該是聖靈的工作”他寫道),不過他也特別討論過埃及。他說:“當聖父降臨埃及的時候,就是降臨在這個塵世。”所以對俄利根而言,如同對但丁一樣,《出埃及記》實際上是一部靈性解放宣言。
俄利根後來在公元前253年遭受了嚴刑拷打後,最終死於羅馬皇帝德西烏斯(Decius)對基督徒的迫害。從那以後,俄利根在主流教會中的命運也同樣令人不勝唏噓。他在世的時候聲名極高,但在後來幾個世紀的教會中卻變得聲名狼藉。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還是因為他對聖父與聖子之間的關係的看法與從4-5世紀發展起來的三位一體學說格格不入。除此之外,後來的神學家也並不是都喜歡俄利根對《聖經》中大部分的內容都不是字面意義上的真理的說法。雖然教會人士一般還是接受他主張《聖經》擁有除了字面含義之外的其它深邃哲理,但他們並不願意承認字面的含義是錯誤甚至(正如我們看到俄利根對伊甸園的詮釋)荒唐的。
新教與直譯主義
如果天主教和東正教對《聖經》的象徵性詮釋本來就不陌生的話,今天令人搖頭的《聖經》直譯主義究竟是從哪來的呢?其實這有部分該怪罪於基督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都將《聖經》奉若權威,但卻從未將其視為唯一的權威:至少教會自己制定的教規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天主教一直都認為缺乏適當訓練的人很容易誤解《聖經》,這也是為什麼教會直到近代以前仍很不鼓勵非專業人士自己解經。
然而,到了近代早期,面對已經變得太過腐敗的天主教,有些基督教領袖(以及許多忠實的信徒)終於認清教會壟斷靈性世界完全是為了一己之私。於是,在與教會徹底決裂的同時,這些領袖——即新教改革家——決定要回歸《聖經》,使其成為唯一可信的權威:這就是sola scriptura,“唯獨《聖經》”的意思。
事情到這裡可能還沒什麼問題,但19世紀傳入美國的新教幾乎全都是由一群沒受過多少教育、從未讀過除《聖經》以外的任何文學作品的人所帶領。這種人在歷史上從來沒少過:中世紀的天主教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曾說過一句話就是在暗諷這種人:Timeo hominem unius libri-“我最怕的就是只讀過一本書的人。”其實不只是美國,其它英語系國家的福音派基督教恐怕最迷的就是這種“只讀一本書的人”。直到今天在美國,你還是可以走進許多人的家裡,發現他們的書架上除了一本《聖經》外啥也沒有。正是因為基督教存在這樣的問題,這才給了原教旨主義崛起的可趁之機。
作為結果,《聖經》的內在含義越來越變成只屬於神秘主義獨享的領域。關於基督的一生,神智學家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曾在《神秘基督教》(Esoteric Christianity)一書中說過:“基督象徵著人類的精神,所以基督存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他出生、生活、受難、復活又升天,‘人子’就這樣親身體驗了世間百態。”因此,基督的故事實際上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道成肉身象徵著我們每個人進入這個物質世界,我們都會在這個舞台上走一遭,最終被釘在時間與空間的十字架上。但是,疼痛與死亡只是暫時甚至虛幻的,因為邏各斯——意識的原理——永遠不會真正死去。它只會改頭換面變成其它形式,不管那是不是我們認得出來的形式(所以在福音書中,門徒有的時候能認出復活的基督,有時認不出他是誰)。
有些人可能會對這些想法感到不耐,並堅持認為這只不過是想要在面對史實考究時避重就輕的伎倆,而這些史實本來才應該成為信仰的基石。但是,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寓言本身又有什麼不對?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出埃及的故事和基督的受難都絕不僅僅是發生在遙遠過去的故事。它們不是盲目的教條,也不是供忠實信徒互相抱團的口號。相反的,它們是對我們內在世界的深刻闡述。從內在的經驗出發,我們才能夠明白“埃及之地,為奴之家”這句話在靈性上真正的含義是什麼,我們可以在自己身上看見邏各斯是如何被釘這個名為時間與空間的十字架上,這並不是避重就輕,反而是在直接傳達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博大精深的真理。
我們甚至還能更進一步。對《聖經》進行寓言詮釋所需要下的功夫實際上比字面直譯要更多。要承認“法老”、“摩西”、“文士和法利賽人”或者是基督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並不容易。很少有人會願意直面自己內在的暴君、偽君子,而能夠看見自己內在的更高本質的人就更少了。認識到摩西這位偉大的立法者其實就是自己,正是走出為奴之家的第一步。認識到基督已在我們身上復活也是在提醒我們要勇於承擔更多責任,而我們對此往往並不是十分樂於承認。
於是乎,我們總是更情願把這些東西放回安全且遙遠的古代——在誰才是出埃及時在位的法老的爭論旁看戲、從不錯過《聖經考古學評論》的最新報導、為最近又有什麼關於史實上的耶穌的新發現激動萬分。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固然可以讓這些問題繼續煥發生機,但卻也注定了我們始終與其保持著距離:它們永遠都是關於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別人”的問題。或許,這才是美國公眾為何始終對《聖經》考古學研究充滿熱情背後真正的原因。
說了這麼多,似乎還是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我們可能太過倚賴於對《聖經》進行寓意解經,如果完全無法再從字面上去解讀的話——即使是在最象徵性的意義上接受它們,這也確實減少了它們原來具有的份量。但這其實是我們自己的目光淺短導致的結果;我們的文明似乎總是無法理解“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29)這句話真正的含義。它並不說要不經思考就盲信,而是在鼓勵我們去認識那些並未直接呈現在我們的雙手和雙眼面前的真相——這就是所謂的“未見之事的確據”。但是,我們往往都抱持著一種葛萊德式(Gradgrindian)的、只願相信冰冷事實的態度,所以我們一向寧可聽從文本,也不願意仔細想想自己內在的感受。一旦我們發現這些文本並不是準確的史實,我們的信心就在傾刻間崩塌了。
縱然原教旨主義的聲音(其實大部分都是被誇大的)在西方似有星火燎原之勢,但信仰的式微終究是擋不了的。假如有天我們都清楚地意識到《聖經》中的許多,甚至是絕大部分內容都不是字面上的事實,屆時會怎麼樣呢?也許我們會像對待奧林匹亞眾神的故事一樣,繼續將它們視為美麗又有力的神話,但這也意味著它們在我們面前從此失去了威嚴。我們會看見古老的神靈被嘲笑和諷刺,就像古雅典的諷刺劇跟琉善(Lucian)的諧劇那樣,所以今天才會有《怒犯天條》(Dogma)和《耶穌基督超級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這樣的電影映入我們的眼簾。
其實這就是新的神話、最新版本的永恆真理產生的機遇。這些新的神話將是什麼模樣還有待觀察;很難想像它們會從如今現存的任何宗教中誕生。在目前所有可以選擇的現實模型中,科學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一個。就像古代的基督教一樣,科學也乍看是要用真理取代神話、用現實取代傳說。這不禁開始令人思考一個問題,不過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在任何正讀到這段話的人有生之年都不會出現:假如有一天,連科學都被證明只不過是一種神話,到時該怎麼辦呢?
____________________
Bibliography
Dante Alighieri, Letter to Can Grande della Scala, Translated by James Marchand, medieval.ucdavis.edu/20B/Can.Grande.html Margaret Barker, The Great Angel: A Study of Israel’s Second Go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2.
Annie Besant, Esoteric Christianity, or the Lesser Mysteries, Reprint, Wheaton, Ill.: Quest, 2006.
Harold Bloom, The American Relig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Israel Finkelstein and Neil Asher Silberman, The Bible Unearthed: Archaeology’s New Vision of Ancient Israel and the Origin of Its Sacred Texts, New York: Touchstone, 2001.
Susan A. Handelman, The Slayers of Moses: 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Origen, On First Principles, Translated by G.W. Butterworth, Repri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hilo, The Works of Philo, Translated by C.D. Yonge,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93.
Albert Schweitzer,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Progress from Reimarus to Wrede, Translated by W. Montgomery, Reprint, New York: Macmillan, 1961.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lated by D.F. Pears and B.F. McGuinness,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理查德・史莫利(RICHARD SMOLEY)是《內在基督教:神秘傳統指津》(Inner Christianity: A Guide to the Esoteric Tradition)、《濕婆的骰子遊戲:意識創造宇宙之謎》(The Dice Game of Shiva: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Universe)、《被禁止的信仰:諾斯底主義的秘密歷史》(Forbidden Faith: The Secret History of Gnosticism)等著作的作者,同時他也是《美國神智學雜誌》(Journal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America,TSA)的編輯,若想瞭解更多可以前往他的網站www.innerchristianity.com/blog.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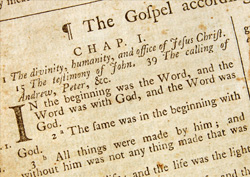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