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GARY LACHMAN
幾個星期前,我有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經歷。跟絕大多數人一樣,過去幾個月來我一直都生活在自願的“居家隔離”之下,乖乖遵守政府為了對抗新冠病毒而制定的規則,這個病毒已幾乎使全世界停止運轉。
我本來就不是很喜歡社交的人,因此保持社交距離、自我隔離和居家防疫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難的。我當然想念與朋友見面、坐在咖啡廳享受悠閒與在書店裡閒逛的日子,但說實話,反正一直以來我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把自己關在家裡讀書或寫作。我在北倫敦所住的街區附近有很多清幽靜謐、綠樹成蔭的後街小巷,因此我每天的運動量,無論是散步還是騎腳踏車,都不成問題。我還有一座自己的小花園,我可以在那裡伸展雙腿、做點舉重。總之,封城對我而言更多只是不便,倒不至於令人窒息。
我得趕緊補充,我知道我有多麼幸運。我絕不是那種喜歡高高在上、對許多不幸的人們正在面臨的困境無動於衷的人。事實上,我上面提到的奇怪經歷就與此,即人類“總是把一切當作理所當然”的根深蒂固習慣有關。
事情是這樣的。一天早上,春天的倫敦通常都是陰鬱的天氣,但在今天卻迎來了明亮溫煦的朝陽,所以我決定打開後門,拿著咖啡到我的小花園轉轉。那天的空氣異常清新——這也算是封城帶來的好處,街上幾乎沒有交通活動——我深呼吸一口氣,伸了個懶腰,抬起頭。不管是清新的空氣還是單純的好天氣,我突然對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充滿了驚歎。我想不出更好的形容了。
那麼,我抬頭看見了什麼呢?太陽。我看見了太陽,並且驚歎不已。
當我說太陽讓我驚歎不已時,我的意思不是它忽然從雲朵後面探出頭來然後大喊“躲貓貓!”,不過當然,若真是那樣的話一定會更令人噴飯、也更值得大書特書。不,太陽沒有任何不尋常,它就在那裡,一如既往,散發黃白色的亮光,因為太刺眼所以不能盯太久。然而,我卻發現我在問自己“那是什麼?”,而當我這麼自問的時候,我忽然明白了什麼。
那是什麼?當然,那是太陽,一個你一輩子都會見到的東西,它已懸掛在那裡將近五十億年,並且預計還會繼續存在五十億年。它是一顆中等大小的恆星,佇立在擁有其它數十億顆恆星的星系之中,而這個星系又佇立在擁有其它數十億個星系的宇宙之中。太陽是一顆巨大的火球,離我們有九千三百萬英里遠,在它身上不斷有氫被轉化成氦,它可以輕易吞噬超過一百萬顆地球。等等。這些東西我都“知道”,但不知何故這些知識並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也沒有解釋為什麼我會突然對太陽感到如此驚歎。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震撼,要是我的鄰居當時也在的話,他們大概會很疑惑我到底在感動什麼。
這種被過去的我一向視之為理所當然、很少花心思去注意的東西所驚艷的感覺,其實與我在疫情剛開始時所感受到的一種奇怪興奮感十分相似。雖然我的生活不至於像其他人那樣便得天翻地覆,但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也不得不跟著改變。有好幾次當我去平常常逛的市場購物時,卻都只能眼巴巴地望著早已被搶購一空的貨架,於是我只好去逛逛那些還沒有遭到歇斯底里的民眾下手的小型雜貨鋪。雜貨鋪的東西往往稱不上齊全,但也只能湊合了。小型的店鋪往往離得更遠,所以我把每天買菜的行程當作額外的鍛鍊,背上背包,然後騎著我的腳踏車出發。我做好了所有大家建議的防疫措施,包括戴手套——當時接觸傳染似乎是最主要的傳播方式——用抗菌劑擦拭我的隨身物品、還有勤洗手。顯然我已經完全進入“危機模式”,但奇怪的是,我卻感覺自己彷彿像在度假一樣。
再次重申,我當然知道過去幾個月對許多人來說宛如地獄,所以我一定要先向他們以及所有站在凶險無比的第一線醫護人員致敬。可是奇怪的是,如前所述,我的日常生活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是的,我確實做了一點改變,但畢竟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變化。但還有一些更詭異的事情。我逐漸意識到自己歷經了一些不尋常的變化,所以我決定嘗試分析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採用現象學(phenomenology)方法來審視我的意識,結果我發現我所感受到的那股奇怪的興奮感其實是一種本質上自相矛盾的自由感(註1)。
自由?我的行動在封城期間被嚴格限制,何況我在允許範圍內的任何行動還要配上重重防疫措施?當我所有的需要與目的都受到比平時更多的限制時——為什麼我卻反而感到無比自由呢?如果這還不夠自相矛盾的話,我最後通過反思得出的結論恐怕會更令人匪夷所思。我感受到的“自由”並不是我最近被獲准重拾的那種自由——對某些已經開始大肆慶祝哪些地方解除封鎖的人來說,自由的意義也許僅止於此。不,我所感受到的是對一種一直以來我都擁有、卻因為習慣而覺得理所當然的自由。是當前的“危機”提醒了我還擁有這樣的自由,就好比我被太陽所驚艷一樣,即使我自以為對這一切早已習以為常。我把我本來已應擁有的自由視為理所當然,如同我認為太陽的存在也是理所當然。結果太陽使我驚奇,我的自由也使我驚奇。
當這種奇怪的幸福感的原因終於呼之欲出時——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方式——我不禁笑了。為什麼?因為我意識到,我正在歷經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在他的許多本書中都描述過的那種意識轉變,也就是從他所謂的“機器人”轉變成“真正的我”或“真正的你”。這種奇怪的轉變是威爾森多部作品中的核心概念,這我再熟悉不過,畢竟我寫過一本介紹威爾森其人的書,書名叫《超越機器人》(Beyond the Robot)。我雖然知道這是什麼,卻把它當成理所當然,就像我認為太陽的存在也理所當然。現在我終於有了親身的體會,這讓我明白了威爾森是對的。
什麼是機器人?它是我們人類經過數千年演化淬鍊出的一種省力機制。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以最少的能量執行最費力的重複性任務,好讓意識有更多空閒去處理複雜的問題。想想你擁有的各種技能,你在剛開始學習它們的時候肯定付出過巨大的努力,比如綁鞋帶、敲鍵盤打字、騎腳踏車或演奏樂器。起初,學習這些事物簡直困難得令人沮喪,我們必須耗費大量的精力,將注意力集中在每一個瑣碎的步驟上,好確保我們的手指能放在鍵盤的正確字母或以正確的方式轉動腳踏車握把。然後我們會失敗、犯錯、跌倒、埋怨。
但如果我們堅持下去,最後總會苦盡甘來。我們發現自己忽然學會怎麼騎腳踏車、用雙手打出一封信——或電子郵件——還有演奏一首曲子。我們已經學會該如何使用這些技巧,這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費心思去注意自己應該將手指擺在鍵盤上的哪個位置,而是可以專心思考我們的電子郵件該說些什麼。這背後的奧妙就是機器人已經接管了繁瑣的工作,讓“我們”可以騰出時間來考慮其它問題。機器人就像一位自動飛行員,讓我們可以在欣賞美景的同時繼續飛行,並且思考抵達目的地後該做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哲學家懷海德(Whitehead)說:“文明的進步意味著不斷擴展我們不需要思考就能完成的重要瑣事。”
要是沒有機器人,我們將一事無成,每次我們想打字、騎腳踏車或運用其它任何技能的時候都必須從頭來過。動物也有牠們的機器人,只是功能和能耐不如我們。你可以教一隻小狗玩新把戲,但牠們終究無法學無止盡。一隻狗也許可以幫你叼來早上的報紙——儘管我懷疑這是一門已經失傳的絕活——但最好別指望牠能學會講法語或縫紉(當然,我知道很多人也學不會...)。
所以機器人是一種方便、或不可缺的工具,我們永遠不能沒有它。但有一個問題。機器人實在把它的工作做得太好了。機器人就像一個僕人,任勞任怨。它很樂意替我們代勞一切,不會有半句抱怨。如此熱心的幫手很容易會開始踰矩、搶走我們寧願自己做的事情。它是如此出色的自動駕駛儀,以至於我們常常忘了自己應該要重新掌舵。這不是機器人的錯。套我前面的比喻,它沒有從我們手上劫機;而是因為我們的放任,才導致它以為我們希望把控制權交給它。而且,它又一向樂於助人,所以自然很願意代勞。
問題是,當我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給機器人代勞後,生活就會慢慢開始不對勁。正如威爾森寫道,機器人有“一個巨大的缺陷”。那是什麼缺陷呢?
“假如我被一首以前沒聽過的交響曲,或是一首詩、一幅畫所深深打動,這個該死的機器人就會立刻開始躍躍欲試。當我第三次聽那首交響曲的時候,它已經急著哼出後面的每一個音符。它完全是用一種自動化的方式在聆聽,使我失去了所有興致。我疲累的時候它最煩人,因為它會趁那時再問都不問的情況下擅自接管我的大部分職能。我甚至發現它在代替我跟我的妻子做愛。”(註2)
(儘管威爾森沒有提到,但我們可以想像他的妻子是否也曾經發現自己被機器人所代勞了)
最終,隨著機器人代勞了所有一切,生活逐漸變得越來越不真實,至少不再像過去那樣真實。這不是突然的變化;它是在不知不覺中慢慢發生。我們對過去從夕陽餘暉、滿天星斗或更簡單地因為一首音樂、一杯葡萄酒所獲得的愜意開始麻痺。就像華茲渥斯(Wordsworth)說的:“牢籠的陰影開始灑下。”我們還是孩子時都曾感受過“永生頌”*,而現在的我們卻空空如也。因為我們已經“長大”了。這便是我們為什麼總是懷念童年的原因,儘管誠如威爾森所指出,我們之所以需要機器人就是為了應付我們還是孩子時反覆無常的情緒與心理變化。在《磐石》(The Rock)中,T.S・艾略特(T.S. Eliot)曾問道:“我們在生活中失去的生命都去了哪裡?”如果讓威爾森來回答,他肯定會回說:“在機器人的手裡。”
____________________
*出自華茲渥斯《憶童年而悟永生》——譯註
有時,與真實生活隔絕的感覺是如此難受,甚至足以導致輕生念頭,或反過來引發突然的暴力行為,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再次“感覺自己還活著”。這是威爾森對謀殺與性犯罪的“存在主義”式研究背後的假設,他在《兇殺案大百科》(Encyclopaedia of Murder)和《走近殺手》(Order of Assassins)中都闡述過這樣的觀點。有些生活幾乎已完全陷入自動化的人會不時爆發殺戮性的憤怒,這種暴力可以讓他們暫時擺脫機器人的束縛。但更多時候我們選擇求助於酒精或毒品這些權宜之計,好讓機器人暫時進入休眠。這就是為什麼往往在小酌了一兩杯後,我們看任何東西都會覺得趣味盎然。詩賦與杜康一直以來都是形影不離的一對也並非巧合。可是,隨著機器人進入休眠狀態,我們做事的效率也跟著受到了影響;所以我們常常被告誡酒後不宜開車。好酒也許可以使人文思泉湧,但還是等神智清醒時再來下筆為妙。
威爾森還發現有另一種方法同樣可以讓機器人暫時離開駕駛座。危機意識是一個很好的催化劑,可以使機器人回到它應有的位置——或者說,讓“我們”回到我們應有的位置。這就是為什麼威爾森習慣把他筆下的角色描寫成“局外人”——他們對目的與意義往往有著更高的胃口,追求“更多采多姿的生活”,這正是現代世界所無法提供的——所以他們選擇奉行尼采的格言,“在生活中與危險為伍”。
威爾森舉了一個例子,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曾說過,他從沒有像在德國佔領巴黎、作為抵抗運動成員,並且隨時冒著被蓋世太保抓捕的那段日子那麼自由過。另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是小說家格雷安・格林(Graham Greene)。格林在還是青少年的時候曾經對生活感到極度厭煩,有一天他找到了哥哥的左輪手槍,於是他決定玩一把俄羅斯輪盤。他將一顆子彈放入彈夾,旋轉轉盤,在光天化日之下拿起槍抵住自己的頭。然後,他扣動了扳機。當格林聽到那一聲咔嗒的時候,他頓時感受到了“無比的喜悅...彷彿一盞明燈被點亮...我覺得,我的生命似乎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註3)
格林一直對生活感到乏味,以至於轟掉自己的腦袋反倒顯得有趣無比。但其實到頭來什麼都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只有他心中的某個部分。“無限的可能性”實際上一直都存在;只不過過去的格林總是對它們視而不見。他沒有看到它們,因為他的機器人在掌舵,而機器人本身就不是被設計來發掘可能性,它只負責確保所有既有的功能可以繼續運行無阻。
正如威爾森指出,當他扣動扳機時,自己可能會就此一命嗚呼的想法使格林陷入了前所未有精神集中,就像用盡全力握緊了拳頭。當他知道這是一發空包彈後,他立刻失去了所有力氣。實際上,在他開始全神貫注的那一刻,機器人意識到了“這很重要”,然後把控制權交還到格林手上。這也是為什麼最後當他可以鬆口氣時,“他”會突然感覺看到了生命的無限可能性。“他”終於又復活了,雖然只是一剎那,但那一刻沒有任何機器人打擾的餘地。
威爾森還告訴我們,類似的事情也曾發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當本來面臨死刑處分的他忽然得知自己獲判緩刑時:一股迅猛、充滿壓倒性的領悟立刻奔襲上他心頭——“一切都美妙極了。”
我們可以用威爾森經常引用的、英國文人塞繆爾・約翰遜(Doctor Johnson)的一句話來總結格林的經驗:“當一個人知道他即將在兩個星期內被處死時,他就會變得心無旁騖。”同樣的道理對沙特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哲學家海德格和神秘學導師葛吉夫都說認識到自己終將一死是一種用來幫助人類克服“存在遺忘”的好方法。一想到我們每個人終有落葉歸根的一天,我們的內心便會獲得一股激勵,使我們想要暫時將機器人推到一邊。
我不會在兩個星期內被絞死,也不會被蓋世太保抓走。但我相信,我所採取的“危機模式”也促使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類似的變化。不知何故,這反而讓我感覺自己變得更有活力。我想,這也是許多在大轟炸中倖存下來的倫敦人後來都會覺得那是他們ㄧ生中最激勵人心的時刻的原因。他們有很多人事後都回憶說,他們從未像那時一樣感到自己充滿了活力與自由。即使他們隨時可能被炸死,但這卻賦予了他們一種有別以往的感受。套威爾森的話來說,發生在眼前的事情降低了我的“冷漠閥值”(註4)。
威爾森使用這個術語是要凸出一個事實:當我們允許機器人鳩佔鵲巢的時候,曾經我們覺得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頓時就會變得毫無意義。我們變得對它們漠不關心,“我們”變得不喜歡正在聽的音樂、正在看的書甚至正在打的炮,這是因為“我們”其實並沒有真正參與其中。我們都知道,當一個人非常沮喪或無聊的時候想讓他打起精神有多麼困難。然而,威爾森卻發現,當愉快的事情已不能使我們振作的時候,麻煩的事情反而能派上用場。麻煩可以把我們從冷漠中搖醒,打破我們很多人都曾深陷在其中的“對一切都無動於衷”之感。說也奇怪,麻煩反而會促使我們必須做出反應,而當它被攻克的時候,我們反倒會發現自己的心情好上了不少。說來矛盾,反而是麻煩使人“醍醐灌頂”。
我之所以對太陽感到驚歎,是因為那天早晨看見太陽的是“我”,而不是機器人。因為“我”是更真實的,因而他看到的太陽也是更真實的。葛吉夫未完成的遺著《只有“我是我”時的生命》(Life is Real Only Then, When “I Am.”)從書名就很傳神地捕捉到了這一點。葛吉夫非常瞭解機器人;他曾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機器、機械,不是真人。或者說,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在沉睡,卻以為自己醒著。這恐怕是“變成機器人”最糟糕的地方:我們以為這種半夢半醒的狀態是真實,絲毫未覺我們其實是在“糟蹋”生命,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真正看見生命的價值。我突然注意到的並不是一個純粹物理意義上的太陽——這些年來我從沒少見過它。機器人習慣把一切它認為無關緊要的東西置之不理,因此它呈現給“我們”的實際上是一個十分簡化後的世界;所有“額外”的東西都被省略了。只有事實,沒有意義。這就是為什麼當它去放假的時候,所有的一切都會顯得格外“有趣”,就像在黑白素描中添加色彩、或為無聲電影放上華麗的配樂。
我們都沒有察覺,大多數時候的我們只是名義上在“活著”,並且把回歸非機器人意識的時刻當成來之不易的“禮物”或“僥倖”,以為那只是重新回到束縛前可以短暫享有的喘息。這些特殊的時刻,也就是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所說的“高峰體驗”其實才是我們的意識本然的面貌,而不是機器人通常被設定的“省力”模式。我們都擁有比我們自己所知道的更多的能耐與力量,但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機器人出於習慣節省力氣,所以從不知道該如何好好運用自己的潛力。葛吉夫非常清楚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他提出了一套我們可以稱之為“徒生困擾”或“以身犯險”的教導體系,迫使他的學生學會去超越這些限制。
不過,就跟真正的危機一樣,人為製造的危機也可能會被慢慢習慣。格林最後也不再玩俄羅斯輪盤,因為把大腦轟掉的感覺已經不再刺激;不得不說,他日後還能寫出他的陰鬱小說真是一個奇蹟。為了讓他的學生不至鬆懈,葛吉夫不得已只好設計越來越難的練習、給出越來越多考驗。在他待在巴黎的最後那段日子,葛吉夫的學生真的是名副其實的“與危險為伍”,他們一群人擠進他的車裡,一邊飆速一邊行駛向他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的地方,直到汽油用盡;葛吉夫實在是一個可怕的司機,他們還得要去找來汽油才能回家。正如一些記述所指出的,有時葛吉夫刻意製造的危機真的太過了,造成一名學生最後終於崩潰。誠如威爾森所言,我們建立文明正是為了盡量避免危機,所以為了感到自己還活著而用槍抵著自己的頭實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威爾森進而提出了他的觀點認為,我們還有另外兩種方法可以擺脫機器人,而且都不需要以身犯險。第一種方法是將精力與注意力都集中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威爾森時常引用赫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寓言小說《東方之旅》(The Journey to the East)中的一句話:“學會專注於每個小細節,這會提升並增強我們的力量。”把時間花在每個小細節上往往會令人覺得索然無味,一旦我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就會給機器人可趁之機。但是,如果我們願意花兩倍的注意力在這些“無聊”的瑣事上——比如打掃我們的家——我們反而會發現,其實做這些事是很愉快的(註5)。為什麼呢?因為是“我們”,而不是機器人在做。樂趣不是來自於這些事情本身,而是因為在做這些事時的我們“活著”。我們可以把這比作是葛吉夫教給他學生的練習;“活著”的感覺就是他所說的“記住自己”,事實上這也正是我們在“感覺活著”的時候所做的事。
另一種方法是利用想像力來在“腦海中”製造危機。這與海德格建議我們要保持對人終有一死的認識是相同的道理。你不妨馬上來試試。現在重新審視你的生活,專心想著所有對你重要的一切。現在,想像一下如果這些東西受到威脅,你會有什麼感受。假如你的房子失火,或是你被診斷出不治之症,也可以想像你像約翰遜所寫的那樣,距離你的死期只剩不到兩個星期。只要你有足夠生動的想像力,應該可以稍微體驗一下如果它是真的會是什麼感覺。
但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如果你能想像失去對你來說重要的東西,你也可以運用想像力來喚起你對將要失去的東西的現實感,因為這就是危機的作用:危機會把機器人推到後面,逼著“你”直面現實。因此,與其在乎失去什麼,不如多想想你現在擁有且絕對會後悔失去的東西能帶給你什麼。這兩種練習的本質都是要喚起一種現實感,只不過正面思考的衝擊效果與負面思考一樣好,而且不那麼令人難受。
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看見太陽以及新冠疫情剛發生時會感到如此興奮的原因。以前我一直把自由當作理所當然。現在隨著自由開始受到限制,我才終於認識到它的可貴;因此,很矛盾的我反而感到更自由了。我所採用的危機模式讓“我”變得更加“存在”,我想起了原來我還擁有這麼多,令我不得不心懷感激。這也可以說是艱難時期所附帶的好處吧。只是如果可以的話,最好還是不要再有一場危機來提醒我這一點了。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A single obsessional idea runs through all of my work: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freedom.” Colin Wilson The Occult (London: Watkins Publishing, 2015) p. xxiii.
2. Colin Wilson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 Novelist’s Approach” in The Bicameral Critic (Salem, NH: Salem House, 1985) p. 39.
3. Quoted in Colin Wilson Frankenstein’s Castle (Sevenoaks, UK: Ashgrove Press, 1980) p. 122.
4. Space does not allow me to tell it here, but the story of how Wilson arrived at this insight is worth telling. I do in Beyond the Robot: The Life and Work of Colin Wilson (New York: Tarcher/Penguin, 2016) pp. 33-34.
5. We can also employ what we can call the “Tom Sawyer effect,“ and pretend that we are enjoying it and then find that we actually do. This refers to the scene in Mark Twain’s novel when Tom pretends he is enjoying painting the fence and by doing so, tricks his friends into paying him to let them have a go. They do enjoy it, so the trick is really on Tom. He has convinced them that painting is fun and their enjoyment ironically proves him right.
加里・拉赫曼(Gary Lachman)曾經是搖滾樂團金髮女郎(Blondie)的創團成員之一,現在則是全職作家,著有十餘本書。他探討的主題包括意識的演化、西方神秘學傳統、文學、自殺以及大眾文化史。詳見他的網站:www.garylachman.co.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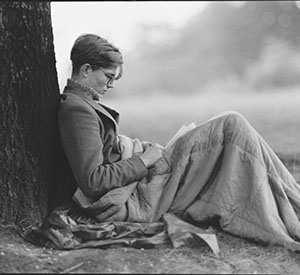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