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JEREMY NAYDLER
在西方的智慧傳統中,人類的遺忘自我(self-forgetfulness)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比方說,我們在柏拉圖的作品、《赫耳墨斯文集》、波愛修斯(Boethius)的《哲學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還有諾斯底教文本《珍珠之歌》(Hymn of the Pearl)中都可以看見這個主題。遺忘自我是指忘記了我們的靈性起源,忘記了我們擁有一個超然的本源。我們通常認知中的人(person)還不是我們的全部,因為在人這個整體裡面有一個精神核心,而我們對它幾乎一無所知,可是它卻是奠基我們存在的基礎,我們如何與它互動也是獲得幸福生活真正的秘訣。
西方和東方的智慧傳統一直在教導人們認識這個精神核心,以盡力人類從古至今總是容易遺忘與忽視我們的靈性起源的壞毛病中力挽狂瀾。但是,今日與過去的不同在於,我們不僅已經遺忘了一部分的自己,甚至也不會再去尋求智慧傳統來喚醒我們的記憶。
相反的,意識的破碎、割裂和離散卻是推動當代文化的原動力。數位革命將這個趨勢推向了極致,以至於我們現在反而是主動設計科技來讓我們分心與遺忘自我,而這恰恰是靈性傳統一直努力想要拯救我們脫離的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實在是做得太好了。結果反過來這又只是導致了更多人無法去注意到,這些發展對想起我們是誰這一最為根本的人類使命究竟有多大的腐蝕性。
不過,除了導致分心和遺忘自我之外,我們的科技也可以變成其它禍害的幫兇,這些東西又更是後患無窮。
非人
在他的生命即將步入盡頭之際,後現代主義思想家讓・弗朗索瓦・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提出了一個直切我們這個時代要害的問題。我們的意識平時總會忽略掉這個問題,它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甚至難以理解,卻也因此更加不容忽視。李歐塔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究竟有多麼重要,所以他ㄧ定要把它攤開來談。他提出的那個問題是這樣的:
“如果有一天,曾經對人類‘適當’的事物,開始變得非人(inhuman)的話會怎樣?”
我們可以把“非人”理解為從本質上對人類來說有害的東西。李歐塔區分了兩種形式的“非人”——一種是我們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的非人化,另一種是侵入靈魂並將其扣為人質的“無影無形”的非人化。後者是兩種中最為陰險的一個,隨著我們與數位設備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它現在也變成了我們的最大威脅。因為我們的科技正在一步步使非人化為現實。
儘管我們已經習於對我們所身處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非人化進行批評與指責,但我們對非人化入侵的敏感神經反而使我們陷入了更大的危機。我們的數位科技很懂得利用這種敏感神經,並一直在無所不用其極地配合人類的喜好來改變自己。透過持續的進化,它們幾乎已經變成了完全符合人類身體和靈魂所需的模樣,它們變得更小、更輕、功能更強也更豐富。
最早的電腦佔地十分龐大,我們不得不在它們前面或周圍來回走動才能進行操作。隨著桌上型電腦的發明,現在終於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下來與它們交流,就像面對面ㄧ樣。今天甚至還能把電腦塞進口袋,還有智慧手錶跟智慧眼鏡這些可以直接穿戴的東西。這些裝置每一次進步,它們與我們之間的交互方式就會又變得更“人性化”,與此同時人類其實也在調整自己配合它們,以便能每天、每小時甚至每分鐘都不跟它們分開。
就在電腦持續重塑人類的身體與靈魂輪廓的同時,人類的內在世界也正在緩慢而確實地被塑造成能與更高級的電腦兼容的模樣——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思考還有我們的日常習慣都受到了影響。在這個不斷發展的共生關係中,我們與電腦越來越如膠似漆,也開始越來越依賴它。生物融合技術已經指日可待。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下一步。
因此,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睜大眼睛認清一個事實,儘管人類是數位科技的發明者、生產者與迫不急待的消費者,但在背後驅動數位革命的其實不是只有人類:還有“非人”也黃雀在後。
我們該如何談論非人這個幽靈?人類似乎總是有一種容易偏離其本質的毛病。對前工業化時代的人,該擔心的是我們會不會退化回宛如動物或野獸般的程度,淪為我們身上還未被重新加工的本能與激情的俘虜。可以說,這是墮落至比人類還要低級的水平的危險:淪落為次人(sub-human)。至於在這個工業化和後工業化時代,人類面臨的主要危機已經不是屈服於本能與激情,而是機器和演算法無情的非人化了。這是墮入非人的危險。
這兩股傾向同時存在於我們的內心,二者都致力於阻撓我們實現人類真正的潛力。但在今天,我們必須特別提防的是非人的危險。非人的目標是要完全取代人類,而且它肯定會成功,前提是如果我們無法以真正的人類之身捍衛我們自己的話。我們必須及早認清人類正在被非人奴役的現狀,並且在充分警惕非人帶來的威脅的情況下,重新找回人性的生活。
人性的生活
到底什麼是人性的生活?如果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也包括了那個我們常常絲毫未覺的精神核心,那麼顯然人性的生活就意味著要開始覺察到它的存在。學會去認識這個精神核心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它是我們最深刻且真實的自我,是我們真正應該尋求認同的那一部分。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進行艱辛的內在轉化工作,好慢慢改變那些過去使我們遠離這個本質的慾望、毛病以及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並從內心裡開始跟它合而為一,智慧傳統一直告訴我們它才是我們真正的存在核心。
轉向並重拾我們的精神核心的道德努力還需要我們願意改變自己的思考方式才能成功。我們要改變只注重結果、為了這個想法就丟掉那個想法的辨析思維,轉而接受重視靜默(stillness)與開放性的沉思思維。波愛修斯想像了一幅美麗的情景,真理的求道者必須將他們徘徊不定的意識變成一個圓,並使靈魂“寄宿在這座寶庫”的中心。他們會在那裡發現比太陽還要耀眼的光,這道光將從內在照亮他們的心靈。
這種“沉思轉向”一直以來都被視為靈性生活的基礎,但它對今天的我們特別重要。我們的科技講求一整套自動化的邏輯分析、計算與問題解決方法,基本上還是辨析思維、結果為重:它們彷彿患有躁鬱症,永遠以一定要產出個什麼東西為目標。相比之下,沉思卻是刻意使心靈靜滯:它不在乎結果,無法被自動化,而且一定要一個人全心投入的參與。沉思能使我們洞見事物更深層次的一面,這是機器思維所不能及的地方。這些洞見將作為強烈的原型形象(archetypal images)從想像世界中湧現,使沉思思維激發更多富有想像力的洞見。這些洞見也會以靈感或直覺的形式猛然乍現,就像一束光照,讓我們得以從更全面的角度看待問題或情境。
沉思經常被形容是在打開靈魂的內在之眼。它也被稱作“心靈之眼”或“心之曈”,透過這雙眼睛,我們便能看見平時肉眼所不得見之事。這種發自內在的覺察不會受到思想和意見的左右,也有人形容這是在打開靈魂的“內在之耳”,令其得以聽見良心的召喚。它會引導我們對什麼該做或什麼不該做產生十足的道德把握,並且鼓舞我們去有所作為。
亞理斯多德堅持,唯有當我們是從對自己身上的這個核心,也就是知性(nous)或“精神智慧的中心”的沉思出發去“下定決心有所作為”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這確實是發自我們內心的作為。任何作為只有從這個源頭出發,才算得上是自由的,因為這時它確實是發自我們內心的選擇,而不再受到任何外在的影響。
根據西方的智慧傳統,任何真正符合人性的作為首先必須是自由的,而它之所以自由也正是因為它發自我們的內心。我們可以看到,亞理斯多德、托馬斯・阿奎那、魯道夫・史代納都曾反覆闡述過這個原則:要是少了自由,我們就絕不可能理解人性的生活的真諦。自由是人性的本質。這並不是說我們每天無時無刻都ㄧ定要動用這種本質去生活,當然不是!但我們現在的數位科技總是有粉碎靈魂的傾向,它一點也無法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相反的,數位科技更像是引入了一場黑暗的洪流,如果我們渴望能發自內心去作為的話,那我們就必須不斷與之抗爭。
自然的內在性
同樣深受數位革命所害的還有大自然,現在人工產生的複雜電磁場已經完全吞噬了自然環境。作為結果,如今不只是人類,而是所有生物都被迫曝露在了遠超過自然水平的電磁輻射之中。最好不要輕易斷言這ㄧ定不會對生物及其身處的生態系統造成任何不利的影響,現在有越來越多研究表明,很多生物其實對電磁場非常敏感,增加電磁場對牠們的曝露確實會產生明顯的有害影響。如此說來,將李歐塔最初提出的那個問題擴大到自然界,變成下面這個類似的問題應該是挺有道理的:
“如果有一天,曾經對大自然‘適當’的事物,開始與自然為敵會怎樣?要是一個充滿生氣的世界被一種不利於生命的力量所滲透了會發生什麼?”
5G的推出只會使地球受到的輻射總量繼續不減反增。5G這項技術將有助於建立全球“電子生態系統”,除了滿足居住在“智慧房屋”中的城市居民的技術需求和願望之外,它也會把自然生態系統與其它生物納入到更無孔不入的監測與控制之下。有朝一日電子生態系統將與自然生態系統互相融合,最終創造出一顆“智慧行星”。
西方的智慧傳統相信其實有兩種自然:有形的自然和無形的自然,或者說是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自然。我們周遭這個可感世界中的所有物質存在都是源自於感官無法捕捉的創造與形成力量,如果我們想完整地把握事物,就必須將它們納入考慮。正是這些力量在供應生命能量,就跟電磁輻射傷害生命ㄧ樣那麼多。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便是要重新找回對這些奧妙的生命力量的認識。
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擺脫對自然的功利主義態度,這種態度只注重收集和分析數據、追求實際的結果,卻一點也沒有觸及自然的內在,好比它也無法觸及我們內在的靈魂生命。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意識狀態——它要更懂得感受、更開放也更能夠共感。對於這種截然不同的意識狀態,歌德曾奉勸我們:
“我們必須全神貫注去聆聽大自然,以期能聽見她的秘密。”
如果我們有幸能聽見,我們會發現原來世間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在訴說一個超然的靈性智慧,而那也是眾生的源泉。對一切受造物滿懷愛意的沉思,會引導我們繼續進入對這個偉大的靈性智慧的沉思,其他受造物和我們一樣都是孕育自這個深不可測的源頭,這就是與上帝合一的神秘之路。
人類遺忘或漠視他們與自然、與神的關係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這讓我們忘記了自己與居住在我們內心中的那個靈性智慧的聯繫。用基督教的方式來說,道/邏各斯(Cosmic Logos)既存在於自然,也存在於人類的靈魂中。
當代的境況使得這些觀點很難受到應有的嚴肅考慮。非人化的功利主義已經掙脫了曾經的道德與精神束縛,隨著電子行業的蓬勃發展以及對“智慧行星”的癡心妄想越來越強烈,一股敵視自然的力量實際上已悄悄潛入了自然的內心深處。這些發展無不使得自然在技術化面前變得越來越無力,利用電腦技術製造嶄新的合成生物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遙控蜜蜂機器人,設計這種機器人的目的是為了將來取代數量正在不斷銳減的真實蜜蜂。諸如此類的事情還只是開始,這個野心勃勃的計畫企圖重新設計世界,以滿足那已經與它的精神根源斷絕了所有聯繫的無情科技意識的渴求。這種意識對生命的神聖性毫無感受,對人類應該向自然負起的靈性責任也一無所知。
這些責任中最重要的就是去瞭解事實真相。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中,只有人類可以全然無私地看見其它生物的內在本質,而不是只想著利用或剝削它們。只有我們才能夠發揮想像力與同理心去設身處地為其它生命著想,透過打開心靈的內在之眼,我們便得以窺見真理。要是我們能經常這麼做,最後我們就可以建立起一個“靈性生態系統”來與那死氣沉沉的“電子生態系統”分庭抗禮,我們的覺察絕對能為這個世界貢獻一些有意義且有益於生命的東西。這既是給我們自己的啟蒙,也是給大自然的禮物,是我們對它的神聖地位的承認。
人與自然是一體的。為人類的未來奮鬥就是在為自然的未來奮鬥。正如我們的生存離不開自然,自然同樣也很依賴我們的覺察與聯繫,因為我們可以用精神之光照耀世界。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Lyotard,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p.2.
2. Ibid.
3.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3.11, poem.
4. The concept of the ‘inner eye’ goes back to Plato’s Republic, 7.4: 518c-d, where he describes how this invisible organ enables us ‘to look straight at reality, and at the brightest of all realities, which is what we call the Good’. Through St. Augustine, De Trinitate, 9-13 (see especially 12: 22-24), Plato’s teaching concerning the inner eye entered the mainstream Christian tradition.
5.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3.3.17 (1113a17).
6. Steiner,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p.140: ‘We cannot, however, think out the concept of man completely without coming upon the free spirit as the purest ex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ndeed, we are human in the true sense only in so far as we are free.’
7. See also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3.3.15-18 (1112b32-1113a9); and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1a2ae: 1.1-4. ‘The whol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man being is summed up by the Fathers in the celebrated formula, “God became man in order that man might become God”.’ Clément, The Roots of Christian Mysticism, p.263.
8. Dante, The Divine Comedy: Paradise, 1.70.
9. See Chapter Three, p.9 with note 22.
10. See Chapter Three, notes 21, 23, 26 and 42.
11. A distinction was commonly made, from the early thirteenth century on, between Natura natura-ta (literally, nature ‘natured’) – the forms we perceive in the world around us – and Natura natur-ans (literally, nature ‘naturing’) – the invisible formative forces that unfold into manifestation.
12. Goethe, ‘Problems’ (Probleme, 1823), translated in Miller, Goethe: Scientific Studies, p.44.
13. As Goethe said: ‘The works of nature are like a freshly spoken word of God.’ Letter to the Duchess Louise von Saschsen, 28 December, 1789, quoted in Steiner, Goethe the Scientist, p.198. Compare with Meister Eckhart who affirmed: ‘All things speak God. What my mouth does in speaking and declaring God is likewise done by the essence of a stone.’ Sermons and Treatises, Volume 1, Sermon 22, p.178.
14. See, for example, Bonaventure, The Mind’s Road to God, pp.20-21. This ‘theophanic view of nature’ is discussed more fully in Naydler,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and the Recovery of a Theophanic View of Nature.
15.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synthetic life-form was achieved in 2010 by Craig Venter, based on digitised DNA code. Venter tellingly said at the time: ‘It is the first species on the planet to have its parent be a computer.’ BBC News, 20 May, 2010.
傑里米・納德勒(Jeremy Naydler)是一位哲學家、文化史學家兼園丁,他著有幾本探討意識歷史的書,同時他也長期關注電子科技對我們內心生活,還有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的影響。他最新的著作是《機器的陰影:電腦的前世今生與意識進化》(Shadow of the Machine: The Prehistory of the Computer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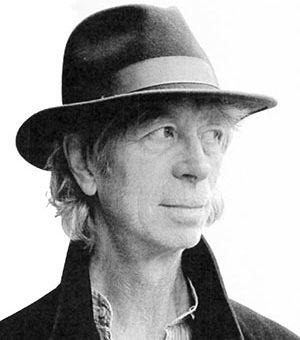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