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KINGSLEY DENNIS
傑里米・納德勒博士(Jeremy Naydler)擁有神學和宗教研究博士學位,目前他以哲學家、文化史學家以及園丁的身份在英國牛津市生活與工作。
長久以來他一直對人類意識的演變史深感興趣,他認為研究過去的文化——相比起我們今天的世俗社會,這些文化對精神世界的態度反倒更加開放——對理解我們如今所深陷的處境,以及開闢我們通往未來的道路都大有裨益。
他也一直都很關心電子科技對我們的內在生活,還有我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所造成的影響,這從他的書《機器的陰影》(Shadow of the Machine)還有《為人類的未來而戰:5G、擴增實境和物聯網》(Struggle for a Human Future: 5G, Augmented Reality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中即可見一斑。
金斯利・丹尼斯(KD):你說科技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這些東西本身,而是它們對人類本質的腐化。究竟科技對人類最主要的威脅是什麼?
傑里米・納德勒(JN):這最早是海德格在他開創性的論文《技術的追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中提出的問題。他說,科技鼓勵我們用一種工具性的方式看待世界,於是我們開始把萬物都當作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再是目的本身。如果這成了我們心照不宣的理解世界的態度,那我們就真的愧對了自己作為人類的身份。我們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失去了對存在之終極奧秘的好奇心,還有我們對生命的神聖感。然後,我們的心逐漸變得冰冷。我們的生活不再有驚奇,反而發現自己與靈性隔絕,就這樣一步步忘記了身而為人的意義。想要真正符合人性的生活,我們便需要始終心存對存在之終極奧秘的感悟。我還要強調,自由是人的本質,可是越是先進的科技往往越是傾向於蠶食我們的自由。我所說的自由是指可以按照我們的理想、目標與價值去生活的能力,而不是那些被強加給我們的選擇。我們的生活遭到技術化的其中一個後果是,我們越來越無法脫離這個受機器主導的世界,反過來變成我們必須盡力配合它,於是我們的自由就受到了侵蝕。
KD:你似乎是在暗示,科技與自然的宇宙秩序或演化秩序是對立的。那麼,科技為什麼會與宇宙秩序產生矛盾呢?
JN:我不是說所有的科技都只會讓我們與宇宙秩序漸行漸遠。有很多科技並沒有造成如此破壞性的影響,不像我們現在那些突飛猛進發展的科技。隨著科學與工業革命,我們集體走上了一條“失道”的道路。人類活動越來越受現代科技的力量支配,這是因為我們已經使自己屈服於一種鐵石心腸的工具主義心態,它催眠我們相信,只要我們能更有效率地利用自然,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富足。因此,科技只是加劇了我們失衡的現況。有誰在目睹了今天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後,還能說我們不是正走在一條與宇宙及自然秩序背道而馳的路上?
KD:你自己已經對你所說的“技術的陰暗面”進行了充分研究。有沒有可能,這些“技術的陰暗面”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人類自己的陰暗面的反映或投射?
JN: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數位革命,還有電子科技的小型化(miniaturization)趨勢,我們會發現這對我們是多麼管用。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想要在現代世界生活,電腦和智慧型手機已變得不可或缺。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這些科技是如何利用我們的弱點。它們無法真正滿足我們更深層次的渴望。相反,它們往往只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遠離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而被更膚淺的慾望所迷惑。這只是影子!或者該說只是其中一道影子。
我們總是在渴求,但我們到底在渴求什麼?我們很容易會誤解自己內心的渴望。因而我們必須不斷捫心自問:到底什麼才能滿足我們?我不認為那會是下一代外型亮眼的IPhone或智慧型手錶。這類閃閃發光的小玩意帶來的“滿足感”通常無法持續太久,因為說到底它只是一個物品。雖然新科技確實可以賦予我們更多能力,但它本身並不能滿足我們靈魂深處的飢渴。
KD:你在最近的新書中提到了“電子極權主義的架構”,你是說我們現在的全球文明正在轉變成一種極權主義形態嗎?
JN:這正是我擔心的事情,而且由於各國政府面對新冠疫情大流行所採取的措施,近幾個月來這一進程又被大大加速了。如今有一個重大的危機正在不同國家中蔓延——即使它們有著歷史悠久的民主傳統——現在公民們已經習慣了緊急狀態下的生活,甚至開始視之為常態。我們迅速接受了政府以保護公眾不受致命傳染病(事實證明,它並不像最初預測的那麼致命)所害為由千方百計限制我們的自由。然後是國家監控、電子定位與追蹤、無現金交易、疫苗護照等一籮筐的東西接踵而至。
由於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國政府的反應可以說是具有一定的默契。聯合國、WHO、WEF等全球組織是最能夠影響政府的幾個主要決策者之一。現在,在WHO和聯合國的力挺下,已經有人提出要建立一套應對這場疫情大流行的全球立法框架。儘管它聽起來完全能自圓其說,但這實在讓我感到非常不安。我幾乎可以想見,在未來只要你沒有接種疫苗,你就不會被允許出國旅行。這很可能就是在前方等待著我們的未來。
義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一直直言不諱地批評義大利政府對疫情的反應,他警告說我們正在迅速滑向一個無底深淵,到時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竟身處在連20世紀的任何老法西斯和共產主義極權政權都望塵莫及的控制之下。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今天許多國家都已經建立且不斷升級的電子基礎設施。
KD:你還談到作為人類控制自然的延伸,電子生態系統將使機器-有機混合體開始篡奪自然有機體的地位。諸如此類的科技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然”呢?
JN:我給你舉個例子,它不完全是機器-有機混合體,而是一種模仿生物體的機器,專門被設計來取代該特定生物的功用。這裡說的特定生物就是蜜蜂,蜜蜂的數量在過去數十年裡急劇銳減。由於蜜蜂的存在對許多不同作物的授粉至為重要,所以蜜蜂數量的減少理所當然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有大量的證據表明使用殺蟲劑,尤其是新煙鹼(neonicotinoids)會對蜜蜂產生十分糟糕的影響,鑒於它們是昆蟲,這一點也不足為奇!但蜜蜂其實對電也很敏感,許多研究指出,大氣中的電磁場飽和是導致蜜蜂數量銳減的一個重要因素。還有什麼比設計一種“機器蜜蜂”來取代真實蜜蜂,更能解決蜜蜂的消失危機呢?機器蜜蜂不會受到任何污染物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盡情操勞它而不必擔心其健康或滅絕的可能性,因為我們能夠大規模地生產它們。甚至機器蜜蜂還不會蜇人。過去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實驗室,其中一座就在哈佛,一直在嘗試研發不同的“機器蜜蜂”,製造將來可以完全取代真實生物的人造生物(但它能造蜂蜜嗎?我可不覺得!)。
你在這裡所看見的正是決心踐踏自然的技術心態,而不是我們應該即刻採取行動來保護蜜蜂,它們的困境反而被當作是一個可以用商業產品來取而代之的機會。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它絕不是唯一一個企圖取代真實生物的科技創新嘗試。
KD:你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們是否有意識到,他們需要將內在發展(“內在轉向”)變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現在我們還能夠抵抗科技支配的方法就只剩下“內在轉向”了嗎?
JN:我既從我自己也從其他人身上一再看到,特別是隨著手機和智慧型手機變得如此普遍後,現在這些東西已經變成了他們的“終生摯愛”,我們開始向這些東西尋求慰藉和心安,就好像它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一樣。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在2005年寫了一本書叫《第二自我》(The Second Self),裡面就是在探討數位裝置對我們產生的心理影響,以及我們是怎麼變得越來越離不開它們。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整個生活都在以某種方式持續“深陷其中”,我們生活在線上的時間越來越長,要是突然失去它們或它們出了什麼問題,我們還會覺得彷彿是世界末日。接受雪莉・特克爾採訪的一些人聲稱,當他們手上的科技產品不能用的時候,他們甚至感覺自己好像失去了生命!就像死了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ㄧ定要開始內在轉向。縱觀世界上的神聖傳統,它們經常提到一個內在伴侶的形象,它有時被視為我們的守護天使,或是蘇菲派的“靈魂的內在知己”,抑或是內在的基督。建立與這個超凡的內在形象的連結是靈性發展的重要步驟。這是要教導我們記住,我們都有一個更高層次的自我,即“會朽者內在的不朽者”,我們必須不斷努力與之連結。這絕非易事!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數位裝置是如何取代了這一更為重要的任務,還向我們兜售一個虛假的“第二自我”或“內在伴侶”,想用來取代我們真實的自我。假如我們能與真正的“內在知己”建立聯繫,我們就可以堅定自己的內心,不再輕易為科技所擺佈。
KD:你還提到了很有趣的一點,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認為電是一種墮落、退化狀態的光。按照他的說法,電之於光好比路西法之於上帝。如今已無處不在的“電磁污染”是不是一種切斷人類與其神聖源頭連結的方式?
JN:史代納對電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觀點。其中之一是我們應該將電理解成是一種亞物質狀態下的光。換句話說,它是低於自然水平、他稱之為“亞自然”的光。出於這個緣故,他警告我們ㄧ定要警惕如今完全奠基在電力之上的現代文明,因為它隨時可能會使我們遠離自然,陷入亞自然的世界。
現在推出5G的其中一個目的便是要加強“全球電子生態系統”,將來我們的電腦,不管是大台、小台還是超級小台的,都必須在其中運作。然而,我們越是依靠電子技術生活,我們就越是與自然疏離。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電子生態系統幾乎成了自然生態系統的競爭對手,因為我們在前者身上投入了越來越多時間,尤其是最近的疫情大流行時期。可是,如果那個由電腦螢幕的光所投射出來的那個世界成了最令我們感到安心的對象,那我們與陽光的關係究竟會變得怎樣呢,更不用說是花香、樹木、風雨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得明白電腦螢幕的光與戶外的陽光到底有什麼不同之處。生活在陽光底下意味著什麼?史代納說陽光是宇宙之道(Logos)的衣裳。他其實是在重申一個非常古老的教誨。我們可以在《詩篇》中看到,上帝被描述為用光之衣包裹自己。我沒有辦法在這裡進一步討論這一點。我已經在書中專門寫了一章。我要說的是,包裹著神的外衣絕對不會也不可能是電腦螢幕發出來的光。
KD:如果人工智慧和電是同一個現象的兩面,那麼我們也可以將人工智慧看作是一種處於“墮落狀態”的能量。你認為人工智慧會是史代納所說的阿里曼(Ahrimanic)的力量的體現嗎?
JN:當我們思考“人工智慧”所指的究竟是怎樣的智慧時,它就變成了一個完全的量化概念。這是一個可以測量的問題,可以通過機器的“每秒運算”來予以衡量。電腦執行邏輯運算的速度非常快,只要程式編寫得當,就可以輸出各式各樣的結果。這當然會給人一種印象彷彿我們的機器已經無所不知,比我們還聰明得多,但那只是空有智慧,而沒有任何真正的理解。它只是一種空洞的聰明,沒有靈魂。
那麼,這種極其聰明、卻又完全冷酷無情的智慧到底體現了什麼呢?我們能說它體現了某種精神生命嗎?如果是這樣,它可能是怎樣的精神生命?回答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觀察人工智慧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例如,當你上網要做什麼事的時候,你需要在對話框和下面的選項中輸入這個那個,勾選這個那個框框,通過辨識一些難讀的文字來證明你不是電腦。只要一個細節稍有弄錯,有時甚至必須得從頭來過。我覺得這實在很令人窒息,因為我被迫得反過來配合這些演算法的要求。我感覺我在這裡碰到的是一些從根本來說簡直反人類的東西。
正是從與這種智慧互動的日常瑣碎經驗,我們才能從中窺見我們到底是在與什麼東西打交道。我認為我們最好還是不要急於命名它,而是盡可能先仔細地觀察正在發生的一切,好比我們跟人打交道一樣,然後我們才能對躲藏在人工智慧背後的到底是“誰?”有一個概念。運用這種擬人化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更好地從生活中的不同的角度持續觀察它的特徵。我們往後還會不斷遇到它,也會在發生在全世界的更大趨勢與變化中一而再再而三看見它的身影。
KD:你曾經說過,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之一便是要“克服我們對微妙的生命力的集體脫敏”,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JN:現代城市生活讓我們失去了對自然的敏銳感知。數位革命的到來更是雪上加霜。為了重新親近大自然中的生命力,你必須花時間擁抱戶外、自然環境、日夜更替、豔陽和雨水。你必須花時間與植物、土壤、昆蟲、鳥類以及其他無數生物建立關係。大部分的時間你其實只需要什麼都不做。你要做的只是敞開心扉,擁抱存在(Being)。這就是海德格所說的“向存在敞開”,正是這定義了人類的本質。使一切如其所是的呈現。透過這種方式,我們便能夠克服對自然界的微妙生命力的集體脫敏現象。
KD:請盡可能簡潔地就人類以及這顆星球上的生命短期內的未來,發表你的看法?
JN:今天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趨勢,許許多多人已開始被捲入其中。許多人似乎覺得他們不再是腳踏在這顆星球上,反而越來越受那個近來開始公然標榜自己本來就是一種“生態系統”的電子世界吸引!這意味著它想要為人類的靈魂提供棲居之地,人們花在網上的時間愈多,他們對地球的忠誠就愈少,要看見這一點並不需要多麼深刻的洞察力。
放棄對地球的忠誠所導致的最常見的症狀之一就是幻想將來有一天拋棄地球、殖民火星。這種幻想現在已經擄獲了一些非常富有且具有影響力的人,例如億萬富翁伊隆・馬斯克還有其他有名的科學家,像是布萊恩・考克斯跟史蒂芬・霍金。這個幻想的言下之意就是要放棄對我們所生活在其上的這顆美麗星球的責任。我認為這種內在的放棄已經發生在了很多人身上,在網絡的教唆與影響下,放棄地球、任其聽天由命的想法現在似乎正變得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這表明了我們迫切需要重新審視自己對自然應負的責任,認識到地球始終是我們人類的歸宿。我們必須忠於這顆星球,承擔這個責任同時也意味著要承擔我們透過閱讀或觀賞影像時,看見我們對這顆星球與我們的同胞犯下的無休無止的破壞,所帶來的愧疚、沉痛與落寞。
然而,我們不能只是自怨自艾,我們要思考自己能做些什麼來治癒自然的傷口。當然,我們可以發起運動、簽署請願書並且在購物前更多三思,但我們其實也應該多多關注距離我們最近的那些事物,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踏實地站在這個地球上。每一座花園、每一片土地,無論它有多麼狹小或樸素,都是我們一親自然芳澤的地方。自然正在邀請我們去照料它,幫助它繼續生生不息。就算沒有花園,我們也還是可以到當地的公園,沐浴在自然下散步,並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的奇蹟上。我們對自然的關注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通過自然,我們才能紮根於地球。
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對未來感到惶恐不安,但這無濟於事。我們需要凝聚力量,心平氣和地迎接未來,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積極且充滿希望的生活。而且我們一定要記住,能夠認識自然,就是我們每個人最好的禮物。只要能對周遭的智慧與美麗有更多認識和欣賞,我們就一定能夠扭轉乾坤。
____________________
金斯利・丹尼斯(KINGSLEY L. DENNIS)是一位全職作家與研究者,他最新的一本書是《劫持現實:人類生命的重新編程&設計》(Hijacking Reality: The Reprogramming & Reorganization of Human Life),他總計出版了十五本書,同時還經營了自己的出版社Beautiful Traitor Books。更多訊息可以參考他的網站:www.kingsleydenni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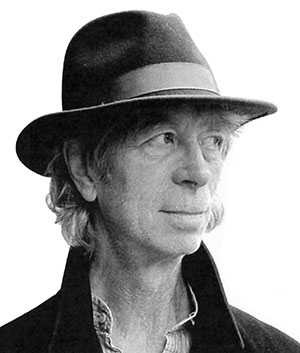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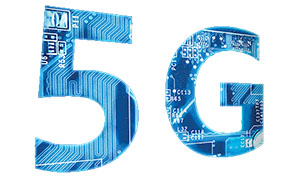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