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henewamerican.com/cfr-still-the-power-behind-the-thr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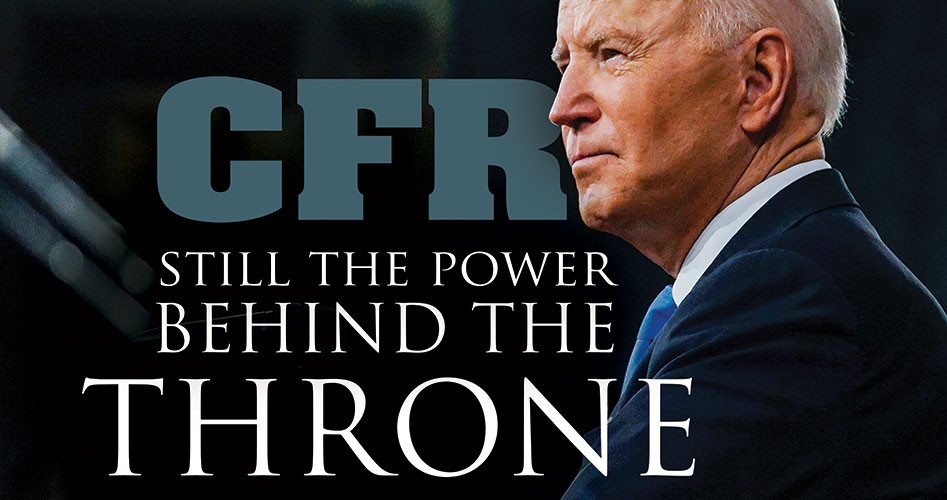
2021年對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來說可謂是別具意義的一年,這個組織經常被譽為如果不說全世界,至少也是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現在打開CFR的官方網站,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歡慶百年”的紀念頁面,上面仔細羅列了這個組織在過去一百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出現在這堆宣傳中的還有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照片、影像和文章,沒有什麼比這些更能凸顯CFR無與倫比的影響力與權力,有好幾百位總統、總理、王子、當權者、政治家、國王、外交官甚至是獨裁者——包括那些大屠殺劊子手——都曾是這個組織的座上賓,或是曾在其著名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發聲撰稿。
CFR不但在政治、金融、商業、媒體還是學術領域都有著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在世人眼中更是頂著“偉大與正義”光環的一流智庫,但是在ㄧ些批評者的眼裡,這個組織恰恰卻是那不受選舉置啄、完全架空了我們國家的“永恆政府”——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中樞神經。
1945年4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劃下句點的前幾天,國務卿愛德華・史特蒂紐斯(Edward Stettinius)匆匆趕到了CFR在紐約市的總部普拉特大廈(Pratt House)。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像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每一位國務卿一樣,前來親眼見證這個組織對制定和形塑美國外交政策的巨大貢獻與影響。”從那以後,這差不多已經成了每一位國務卿的慣例。史特蒂紐斯和他往後的幾乎每一任國務卿都是CFR的成員——只有川普政府是一個例外。現在,隨著喬・拜登入主白宮,CFR再次取回了對國務院的控制權,這回接任國務卿的是CFR成員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其他CFR成員則填補了政府機關和拜登內閣中的一些位高權重的職位。
作家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和伊文・托馬斯(Evan Thomas)曾以“智者”(The Wise Men)來形容CFR最重要的那些領導人物,而CFR自己控制的學術和媒體班底也從不吝於使用這個動聽的稱謂來奉承自己人。既是記者也是總統講稿撰稿人的約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對CFR有一個頗有名的評價,他說這個組織基本上就是“政治家的必修學校”。普立茲獎獲獎記者、歷史學家大衛・哈爾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則形容CFR是“建制派的非官方俱樂部”。歷史學家、總統顧問小亞瑟・施瓦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亦直言CFR完全可以說是“美國建制派核心”的“橋頭堡”。與國務卿史特蒂紐斯一樣,說出這些恭維之言的人們自己也都是CFR的一分子,雖然他們往往諱於聲張這一事實。
然而,從同樣是CFR成員的作家兼記者理查德・羅維爾(Richard Rovere)口中,我們卻看到了CFR令人不安卻也更為寫實的另一面。“CFR的主席們,”他說:“就像是某種主席團〔Presidium,共產國家的常設立法委員會——譯注〕,為指導我們國家命運的建制派出謀劃策。”羅維爾用“主席團”這個字眼可謂是恰如其分。他顯然是在拿CFR與曾活躍於蘇聯,且迄今仍然存在於中國和北韓等共產主義專制國家中的那些冷酷無情、不需選舉、不對人民負責的結黨集團相提並論。就是這樣的組織在“指導我們國家的命運”,這樣的想法實在足以令每一個美國人都感到寒毛直豎。可是,羅維爾本人的這番話其實是在恭維他的CFR同志,而不是譴責他們,而我們也知道數十年來CFR的精英實際上一直在與共產世界的精英眉來眼去,相比起受憲法制肘的有限政府,共產主義專制毫無疑問才更投普拉特大廈的諸侯們所好。
任何熟悉CFR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背叛、叛國、顛覆和勾結這幾個字眼基本上就是對這個組織百年來的是是非非最好的總結。這樣的指控也許刺耳,但絕沒有誇大,我們很快就會明白箇中緣由。CFR的歷史就是一部長達一個世紀的國家主權顛覆史,也是一部企圖建立全能世界政府的奮鬥史,這個世界政府就是CFR成員口中常常出現的“新世界秩序”。
然而,儘管CFR有著清一色都是美國社會政商顯貴的成員,足以在全球事務中呼風喚雨,而且還總與歷史進程的推動者與破壞者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大多數的美國人卻依然從未聽說過有這麼一個組織的存在。當然這正是CFR的領導人所樂見的,因為他們更願意在幕後發號施令。他們選擇躲藏在陰影中不是因為謙虛;而是他們很清楚一旦他們將自己的議程開誠布公,那勢必會招致美國人民一致上下的強烈反抗。過去二十年來,CFR開始越來越常拋頭露面,比如其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和其他CFR的發言人與“專家”就經常以智者的姿態出現在主流媒體舞台,就各種議題向群眾分享他們的智慧。這些傢伙日益高漲的名聲並沒有帶來任何真正的透明度,但是對那些願意睜開眼睛、動腦思考的人來說,這四年和過往幾個月以來所發生的一切,已經完全足以打消任何對深層政府的存在及其暴政陰謀的懷疑。
看著這些年來從不間斷的針對川普總統、他的家人、他的政府還有他的支持者的窮追猛打——發出這些砲火的不僅有“自由派”媒體和“進步派”民主黨人,甚至還有新保守主義者、“溫和派”共和黨人以及許多資深政府官員(有些已經退休,有些還在任職)——數以百萬的美國人終於恍然大悟,他們憤怒地驚覺不光是在我們政府的最高層,而且還包括我們整個社會的權力頂端,都存在著一股處處要與川普為敵的力量。
如果你是才剛剛醒悟沒有多久的人,那麼你一定得瞭解這股敵對力量——左派教授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和保守派專欄作家伊蒂絲・羅斯福(Edith Kermit Roosevelt)用“權力精英”來稱呼他們——絕不是近年來才開始出現的現象。如前所言,一個世紀以來,CFR的深層政府一直處心積慮在拓展其權力,耐心地等待時機滲透和腐蝕我們的一切立國之本。
CFR的創始人也是一戰後功敗垂成的國際聯盟的起草人與宣傳者,後來仍然是這同一群人在二戰後創立了聯合國,從那以後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的各種聯合國機構和國際組織背後,幾乎都有這群人的身影。這些人幕後推動了許多旨在從各方面削弱美國、同時幫助我們的敵人一步步坐大的破壞性政策。利用聽話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CFR跟他們的馬前卒制定了無數禍害萬千的政策,現在他們距離徹底消滅我們所熟知的自由以及我們的立憲共和國,幾乎只剩下一步之遙。舉例來說,正是他們在提倡和從旁煽動開放國境、不可持續的支出與稅收政策、無止盡的對外援助、LGBTQ“多樣性”政治正確、種族對立分化、選舉舞弊、槍枝管制、軍隊的女性化(feminization)與政治化、狂熱的環保主義、全球暖化歇斯底里、新冠恐慌和醫學專政、川普恐懼症、假新聞、科技公司審查、壓迫性監管、把我們的工作與技術外包出去的貿易政策、充滿共產國家色彩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聯邦政府篡奪州權和州政府、向我們的兒童和青年灌輸道德淪喪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諸如此類。
深層政府出場
CFR的精英們歡慶2021年不只是因為這是他們組織成立的百年紀念,更是因為他們已經透過上述的所有毀滅我們國家的方式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他們成功趕走川普,並且用他們最喜歡的候選人-喬・拜登取而代之。拜登本人不是CFR的一員,但他卻讓普拉特大廈的“智者”順利入主內閣,並且在幾乎所有川普曾經反對CFR全球主義者的新世界秩序議程上都重新改弦更張。拜登曾經在2018年1月23日拍攝於CFR總部的一段錄影中說過一些意味十分深長的話,錄影中CFR主席理查德・哈斯先是自我介紹,然後又開始細數他在CFR的工作,拜登則在一旁打趣說:“而我為理查德工作。”這應該只是一個單純的玩笑話,對吧?但俗話說得好:“戲言寓真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希拉里・柯林頓,在擔任國務卿期間,她曾在CFR於華盛頓的新辦公室裡承認,她已拜訪過紐約的“總部”不下好幾次,不過有了這間新辦公室,一切就方便多了。“我們從CFR那裡得到了很多建議,”她說:“這樣我就不必繞太多遠路,我們都被清楚交代了自己應該做什麼,還有我們該如何謀劃未來。”
被CFR全球主義者團團包圍的喬・拜登同樣也是依靠這個組織來指點江山,告訴他怎麼做、該怎麼思考——看著拜登越來越惡化的健康狀況,我們不禁懷疑在幕後操縱者的手下,他到底還有沒有哪怕一丁點的自主餘裕。話雖如此,拜登對那些顛覆性議程的忠心耿耿倒是無需懷疑。雖然CFR掌控的假新聞媒體不斷努力將拜登包裝成是溫和派或中間派,但他在擔任參議員三十六年,還有擔任歐巴馬的副總統八年來的表決、言論和作為,早已將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曝露無遺。除了作為職業政客的官方資歷,拜登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也曾不止一次在多個場合表達過他心中真正的想法。比方說,他在1992年為《華爾街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為〈為何我開始認同新世界秩序〉(How I Learned to Love the New World Order)的文章。除了聳動的標題,拜登這篇投書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他提議應該“讓《聯合國憲章》能夠動起來”,也就是為聯合國建立一支永久性的軍事力量。
與拜登在《華爾街日報》上的這篇投書的內容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文章刊登的時間。當時喬治・布希總統正在電視上反覆提起新世界秩序,並且開始派遣大量美軍前往伊拉克,據布希自述,這麼做是為了“證明聯合國真的能像其創始人所期許得那樣運作起來”(我們稍後會再回來談談這些“充滿遠見”的聯合國創始人)。所以,拜登這位全球主義民主黨人是注定要接過同為全球主義者的共和黨人喬治・布希的新世界秩序大業。事實上,不管是拜登、布希還是其他成千上百位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政黨對他們來說都只不過是一個標籤,好掩飾他們實際上都是CFR的馬前卒,都是崇尚全球主義的統一黨(Uniparty)。
喬・拜登:CFR在白宮的傀儡
還想要更多可以證明拜登有多麼忠誠的線索嗎?當拜登和吉兒(Jill)在1977年結婚的時候,他們選擇的婚禮場地是紐約市聯合國廣場的聯合國教堂中心(CCUN)。CCUN這個組織標榜自己是“通過聯合國的大門”,並且也是聯合國“世界秩序”(World Order)計畫的堅定支持者。CCUN大樓在1963年9月落成,當時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CFR成員)、美國國務卿迪安・魯斯克(Dean Rusk,CFR成員)都有出席剪綵典禮。這座教會中心是由全國教會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負責管理,該理事會則受洛克婓勒家族資助,主張從基督教的立場出發支持世界宗教與世界政府。後來,激進女權主義組織-聯合衛理公婦女會(United Methodist Women)接手教會中心,並一直持續經營至今。
明明不管在華盛頓特區、紐約還是他的老家特拉華州都有數不清的天主教教堂可任君挑選,“虔誠的天主教徒”拜登為何卻偏偏要選在聯合國教堂中心舉辦他的婚禮呢?當然選擇這間教堂更符合他支持墮胎與LGBTQ的“婚姻”立場,這些立場儘管與天主教教義相衝突,卻完全符合聯合國所意欲推廣的議程。2021年1月21日,在政府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上,當白宮新聞秘書珍・莎琪(Jen Psaki)被問及拜登支持墮胎是否與他的天主教信仰有衝突時,她立刻回答說:“我想藉這個機會提供各位,他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經常上教堂。”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回答媒體的老套路,不僅僅是拜登,南希・斐洛西(Nancy Pelosi)、安德魯・古莫(Andrew Cuomo)以及其他所謂的“天主教”政客僅管再怎麼違背他們教會的教義,依然不厭其煩標榜自己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歐巴馬也曾稱讚他的新聞秘書比爾・柏頓(Bill Burton)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還有吉米・卡特,甚至連比爾與希拉里・柯林頓都是這麼自居。
所有這些都只是證明了“偽善是邪惡對美德的致意”這句格言是多麼不假。儘管如此,一向藐視基督教道德的全球主義政客們還是很清楚,大多數美國人都仍然自認是基督徒。因此,謹慎的政客(像是拜登)會故意選在教堂拍攝競選宣傳照,還有時不時在演講中引用幾句《聖經》或上帝的話。但拜登的演講撰稿人卻恰恰在最需要的時候“忘了上帝”。我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拜登可以ㄧ邊在全國祈禱日的七十週年活動上專心“禱告”,ㄧ邊卻ㄧ句話也沒提起上帝。這可是有史以來頭一遭!“虔誠的天主教徒”拜登在他的演說中一次也沒有提到上帝、耶穌或《聖經》,反而是繼續大談充滿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清算種族正義”、“氣候變遷威脅”還有其它各種政治正確主張。這完全符合深層政府企圖在美國實行的去基督教化運動:先是將上帝和祈禱從公共場所中去除,然後是把上帝和祈禱也從祈禱中去除!
想必拜登在祈禱會上心裡念念不忘的還是卡爾・馬克思。他一直都惦記著世界經濟論壇(WEF)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以及“大重置”計畫,這項計畫企圖“重置”這整顆星球——涵蓋政治、經濟、社會、道德與靈性——好使它們都更能符合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構想。根據WEF的官網,“新冠疫情提供了我們一個可以選擇以更加可持續的方式,來重置與重塑世界的機會。”它還呼籲我們每一個人“想像這樣一個世界,我們所有人都能夠依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來構造自己的生活。”正如《新美國人》(New American)雜誌一直以來所報導的,SDG就是聯合國《2030年議程》的核心,這是聯合國意圖徹底掌控地球上的一切人事物的計畫——講好聽點則是為了拯救“自然環境”、建立“公平正義”。正因如此,世界上最富有的億萬富翁和他們手下的政客才要千里迢迢搭飛機到瑞士達沃斯,在2020年WEF的年度香檳與魚子醬派對上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就是你我啦)宣布,我們大家都必須勒緊腰帶,最好不要開車然後少吃肉,乖乖聽從嚴厲的管制(封城、戴口罩和疫苗護照)以及其它許許多多瑣碎的規定。WEF在2020年打出大重置,與拜登的上台簡直是天作之合。
拜登內閣才剛在白宮展開他們的百日新政,就迫不急待地開始履行WEF-聯合國的那些與新冠疫情或全球暖化有關的“危機”計畫。拜登宣布美國會再次加入聯合國的巴黎氣候協議,這是歐巴馬當初非法(未經參議院批准)硬施加給我們的東西,直到後來川普才下令退出。拜登還效仿中國共產黨的中央計畫,對碳燃料發起了政府規模的迫害,然後祭出了一份總計兩兆美元的氣候協議,還被參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評論這與她提出的社會主義綠色新政堪稱異曲同工。拜登還進一步表示,他已決定撤回川普先前的決議,會重新向聯合國手下那可恥的WHO繳錢。川普原定要讓美國在2021年7月退出WHO,現在也被拜登收回成命。
拜登在所有這些領域都忠實地履行了WEF和聯合國的“全球治理”計畫。同時這也遂了CFR的如意算盤,這並不奇怪,因為不論是WFE還是聯合國的成立,CFR都功不可沒。那些最頂尖的CFR成員不僅經營著WEF,甚至還可以在其光鮮亮麗的晚宴上出任主持。億萬富翁大衛・魯賓斯坦(David M. Rubenstein)是CFR主席(以及凱雷集團的聯合創辦人與執行董事),同時他也是WEF的董事之一。其他同樣坐在WEF董事席的CFR成員還有賽富時公司的創辦人兼執行長馬爾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貝萊德集團的執行長勞倫斯・芬克(Laurence D. Fink)。前美國參議院與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CFR成員)現在是拜登的“氣候特使”,也是達沃斯的常客,今年一月他才在達沃斯的特權人士們面前盛讚了大重置計畫一番:“我認為大重置會以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更快也更猛烈的方式發生。”凱瑞,又被稱為拜登的“氣候沙皇”,他現在已在國家安全會議中取得了席位,這幾乎就是拜登政府向CFR發出的信號,表明它已聽從後者的指示,將氣候變遷視為國安問題,從而證明——甚至是要求——政府為了面對氣候變遷而採取更多管制措施都是莫可奈何。按照那些氣候變遷狂熱分子的說法,這意味著幾乎所有人類活動都需要受到管制。
CFR再次獨攬大權
凱瑞並不是唯一一位獲拜登政府任命的CFR成員。事實上,拜登的內閣和那些高檔“公僕”又重新走回了CFR的白宮馬廄老路。CFR幾十年來一直都緊緊盤踞著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從羅斯福到歐巴馬——從共和黨到民主黨政府——CFR自始自終都在扮演著“隱形政府”的角色,這是誓言捍衛憲法的作家、前FBI特務丹・史穆特(Dan Smoot)在他出版於1962年的同名著作中對CFR的諷刺。從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國防部長洛伊德・奧斯汀(Lloyd Austin)、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國土安全部長亞歷杭德羅・馬約爾卡斯(Alejandro Mayorkas)、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CIA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到白宮新聞秘書珍・莎琪(當然還不止這些),都是拜登——或者是他背後的某人——找來填充我們政府高層的CFR成員。還有很多重要的空缺有待填補,這些職位想當然一定也會落入普拉特大廈那群人的手中。
為什麼像CFR這樣全由權貴組成的半秘密俱樂部明明已經支配了我們的國家,這件事卻從來沒有成員眾所關切的焦點——至少是新聞報導或討論的主題?這當然要多虧CFR擁有超過五千名成員,這些人都透過旋轉門(revolving-door)來在企業、慈善機構、媒體、學術界還有智庫間來回穿梭,最後再回到政府“為民服務”。
華爾街精英銀行家/律師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是CFR在1953-1970年的主席,也是先後九位美國總統的顧問,更享有“建制派主席”的響亮名號。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他親自解答了他是如何使用CFR的成員來遞補政府的高層職位。“每當我們需要人的時候,我們就會翻開CFR的成員名單,然後撥電話到紐約。”麥克洛伊說。他的繼任者,大衛・洛克菲勒也是如此,洛克菲勒的繼任者仍是如此。根據CFR的2020年年度報告,總共有三百七十四名成員在政府部門任職。想像一下,如果擁有五百五十萬名成員的全國步槍協會也能在這麼多重要的職位上佔有相應的比例,到時媒體會如何急著抗議!或者也可以改成基督教保守派團體,像是擁有七百萬名成員的全國生命權協會(National Right to Life)、擁有兩百萬名成員的哥倫布騎士團(Knights of Columbus)或其它任何團體。但說再多也無濟於事,因為CFR的成員早已牢牢把持主流媒體。簡單來說,一切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包括所有那些三個字的“新聞”媒體——ABC、NBC、CBS、PBS、CNN、NYT、WSJ、FOX、NPR都不過是CFR的傳聲筒,它們全都只是想要說服我們相信“此地無銀三百兩,快滾”。
只是“陰謀論”?
然而,CFR所行使的權力與影響力卻遠遠超出了其成員在我們的政府、媒體界及其它美國的權力機構中所能施展的程度。CFR在英國還有一個對應的機構,堪稱它的姐妹組織,即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RIIA),也稱查塔姆大廈(Chatham House),其與CFRㄧ樣是誕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最近幾年,CFR還創建了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CFR)和關係理事會(CoC),來負責統籌來自包括俄羅斯與中國等二十四個國家裡的CFR相關附屬組織。此外,CFR也與大衛・洛克菲勒創立的三邊委員會以及超級精英的秘密組織-畢德堡俱樂部關係緊密。CFR成員在世界銀行、IMF還有聯合國也同樣都把持著重權。最重要的是,它的成員現在遍佈大企業、大銀行、科技巨頭、數據公司、媒體巨頭、製藥巨頭等全球大咖。一言以蔽之,CFR擁有的影響力絕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
每當有人對CFR的巨大影響力提出質疑,它的合作者/擁護者就會立刻回以萬用的“陰謀論”來作為反擊,只要被貼上這個標籤,就可以讓任何質疑者瞬間名譽掃地。喬治・加夫利里斯(George Gavrilis,CFR成員)在不久前才出版的新書《外交關係協會簡史》(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 Short History)中就介紹了這種嘗試通過開玩笑打太極的方式來打消公眾質疑的方法。他在書中提到“還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理論,聲稱CFR與外星人陰謀論有關。”“時間回到1945年,”加夫利里斯寫道:“艾森豪在摩洛哥秘密會見了外星人,後者任命了第一位常駐美國的大使。在CFR的幫助下,政府成功對美國人民隱瞞了外星人的存在。”是的,你沒聽錯,那些頭戴錫帽的神經病和飛碟裡的外星人都可以被跟CFR攪和在一塊。透過抹黑和嘲諷來打壓批評者的聲音,或許對傻頭傻腦的人還有點用,但成千百萬的美國人如今已越來越不吃這套,他們雪亮的雙眼都看見了我們這個國家正在向無可挽回的方向急速邁進,至於是哪些人正在將我們引向那裡他們也都看在眼裡。
羅斯福的顧問、華爾街銀行家詹姆斯・沃伯格(James P. Warburg)曾在1950年2月17日當著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的面告訴他們:“無論我們喜不喜歡,我們都將擁有一個世界政府...不管那是要通過說服還是征服來實現。”他本人非常認同世界政府的構想,也會盡一切全力來推動它實現。沃伯格也是CFR成員,他的父親保羅・沃伯格(Paul Warburg)亦然,後者甚至還被譽為是聯準會之父。許多著名的CFR成員都有過類似的發言,他們亦都利用各自的權力在努力推動CFR的世界政府議程。隨著新冠疫情、氣候變遷“危機”沓至而來,CFR及其全球主義盟友正在加緊腳步實施大重置,以便一舉消滅全世界的中產階級,好將所有的權力——包括政治與經濟——通通都集中到他們自己的手上。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已經有無數勇敢的美國人開始出面揭露陰謀——這絕對不是“陰謀論”——最後卻只換來了世人的嘲笑與譏諷。除非有越來越多美國人開始覺醒,認清CFR的滲透已經到了何其無孔不入的地步,並挺身反對其邪惡的新世界秩序議程,否則深層政府對我們的國家——還有這整個世界的殘酷支配永遠也不會有被打破的一天。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